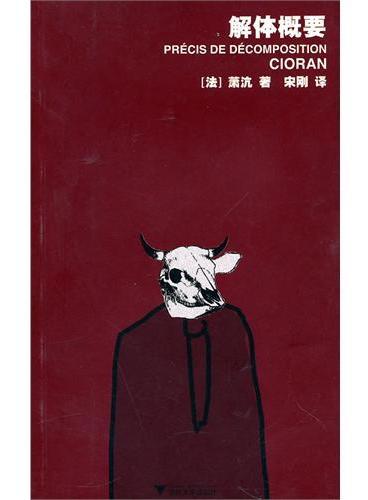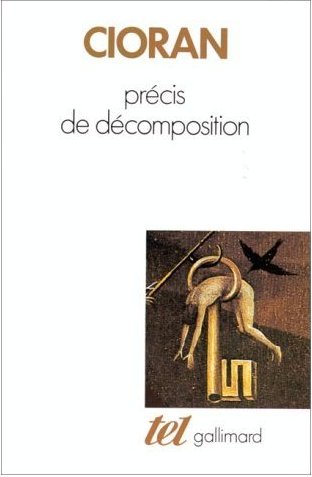图说:齐奥朗《解体概要》
孤独总是如此耀眼,这让隐士万分沮丧。世间的悖论比比皆是,这只是其中例证之一。齐奥朗深谙孤独之道,这位罗马尼亚裔法国哲人在笔记中写得明白:“我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这是我唯一的目标。重返隐居生活!让我为自己创造一种孤独,让我用尚存的抱负和高傲在心灵中建起一座修道院吧!”他的著作预示着这心灵修道院的落成,可是他哪里知道,现在这修道院已经成了旅游胜地,好奇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为这建筑的阴森和幽暗所吸引,全然不顾建造者从角落里投来的厌恶目光。还好,齐奥朗已经长眠于绝对的孤独之境——死亡,他的著作掀起的世俗波澜不再可能惊扰到他,否则那犀利的唇舌间又将吐露何等可怕的诅咒。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诅咒只会引来更多“游客”,因为人类需要诅咒不可替代的解毒作用……
齐奥朗深知,所有激烈的东西都同时拥有天堂和地狱,这才是他情之所系。天堂那高高在上的位置飘渺而不真实,通向天堂唯一可靠的途径就是跳下地狱,它的灼伤也就是天堂的狂喜。面对来自上天的召唤,齐奥朗最经典的姿势却是静默,他的“无从应对”将自己抛掷到他所眷恋的字词中,他因而得救?至少,他还来得及写下那些充满魅力的诅咒:对于圣洁泪水的唾弃,对于疯狂先知的讥笑,(“高贵只有一种,就在对存在的否定中,在俯瞰断壁残垣时,那一抹微笑里。”)灵魂强加于精神的任务被一笔勾销。他仍然处在悬搁状态,立于天地之间,思想所携带的词语之河川流不息。生命,什么也不需要证明;文字在自身的神秘中仅仅是模模糊糊地抓住了它。永葆存在的激情——齐奥朗所有著作指向这一行字。
这样的孤独带来茫然的自省。“大地、天空,是你修炼间的四壁,而在没有任何生气拂动的空气中,唯有预言的缺席占据着一切。”往内心深处挖掘的孤独离时代越来越远。齐奥朗和他所推崇的克尔凯戈尔、尼采一样,一心只从自我的深处去汲取思想,陷溺在他们的缺陷所修饰的永恒里,而他们的战栗和热量倒有可能给平庸的时代带来创造自身传奇的可能。这种毅然地向内挖掘如此艰难,齐奥朗著作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格外滞重,让人忍不住要仁义地为他画上句号。可是晃晃悠悠,这些句子仍然在倔强地向前发展着,带着人们前往不曾见过的墨汁般的黑夜。桑塔格在《“自省”:反思齐奥朗》一文中,也不忘指出:“齐奥朗写作的特色是,他用以开头的正是别人用以结尾的。由结论开始,他就是从这里开始写。”这是外在的观察,其实这正是由齐奥朗持续地向内心掘进的写作方式所决定的。尽头的尽头永远是黑暗,但也还有温暖的热度,这是上天给予倔强者独特的奖励?对齐奥朗最起码的尊重,就是在有关他的任何结论后面,你得加上一个问号,如此你才敢于迎接他恶毒的、布满血丝的眼神,何况他的文字下还埋藏着尖刀。
《解体概要》一书就三次提及这件“凶器”。在《狂热之谱系》中,齐奥朗写道:“人一旦拒绝承认思想观念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就会发生流血……坚定的决心下面竖着一把尖刀;满怀激情的眼睛预示着凶杀。”在《恶人的模样》中,他又写道:“他额顶匕首,遐思满腔,而又好像是在动手之前,就已经对一切罪行感到失望。”在书的末尾《箴言家的秘密中》一文中,他又提及:“欢乐给人以致命的打击欣喜在微笑之下掩藏一把匕首。”无论是决心还是微笑,在齐奥朗的眼里,其后都隐藏着尖刀。不是因为这决心和微笑有多狡诈,而是这尖刀原本就隐藏在齐奥朗的视线之中——在齐奥朗的著作中,这尖刀其实无所不在。他习惯于用它在世俗的观念上划一道口子,然后贪婪地盯着从伤口里慢慢往外渗透的鲜血;齐奥朗正是用思想的暴力赋予思想和观念本身以新意,或者还怀有对他讥讽过的“深刻”隐隐的期待。对此,齐奥朗在《缩短的自白》一文中作过正面表述:“我只愿在爆发性状态中,在狂热或高度紧张中,在一种清算气氛,一种痛斥取代打击和伤害的气氛中写作。”疯狂、热烈、恶心、深渊、憎恨、恐惧、厌恶、癫痫、腐烂、魔障等等重量级词语充斥着齐奥朗的著作,从中我们可以依稀勘探出这是怎样一个灵魂。波德莱尔曾经说过:“要看透一个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搜寻那些最常见的词,这样的词会透露出是什么让他心驰神往。”虽然这些词语被一条优雅的思维逻辑链条捆束在一起,因而减轻了负重,但毕竟是它们构筑了齐奥朗著作的底座,借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仇恨的历程,其用意竟然是捍卫腐败?这个沉迷于恐怖之词的灵魂,习惯于观察和表象正好相悖的“真相”:“‘真相’只有在精神忘掉了建设狂谵,不知不觉滑过了道德、理想与信仰的瓦解阶段时,才会显现。”如此“捍卫腐败”,其实意在对所有“正义”之词的质疑,只有那些分崩离析的时代,才有幸向我们裸裎生命的本质。
图说:E.M.齐奥朗
综观齐奥朗著作,他的行文有着一流诗人的语感和讲究,颇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因而引来诗人们的赞许也就顺理成章了。196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就曾说,齐奥朗“是瓦雷里之后,最伟大的法文作家之一,足令法文增辉”。对于这样的赞誉,齐奥朗一定会欣然受之,尽管在我看来瓦雷里是更优雅和绵密的思想者。瓦雷里和齐奥朗都专注于内心的省察,不过仅就自省的精微程度,瓦雷里显然更胜一筹,思维之翼的每一丝颤动都逃不过瓦雷里笔尖的追逐,齐奥朗则在思之力度上做文章,他是拿着一把匕首在做刺绣的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偶尔不小心弄得鲜血淋漓也就可以理解了。诅咒似乎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看看这位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系出身的人物对哲学的咒语吧:“我背弃哲学,是在发现康德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种人性的弱点,听不出一丝真正的哀伤以后。”“哲学工作没有生命力。”“我反对哲学,所以痛恨一切无动于衷的思想。”他甚至在《哲学与卖淫》一文中,以他特有的恶狠狠的语气将哲学家贩卖自己的思想比作妓女们贩卖自己的身体。与此相应,齐奥朗毫不迟疑地站在诗歌一边:“思想可曾写出过一页东西,达到过约伯的哀鸣、麦克白的恐惧或一曲和声的高度?”在《知识的布景》一文中,他说得更加明了:“哲学并不会比诗歌更严谨。”这些认识,使齐奥朗对所有体系化的思想持一种否定态度。是啊,谁能在漫长的庞大哲学体系建设中保持足够的激情呢?他甚至不放过那些哲学体系的基石——哲学概念,他把这些概念放置在带有锋利刀刃的思维之轴上来回切割,直到它们溃散成“一片温柔散淡、厌倦知识的麻醉液体”。
这也解释了齐奥朗何以喜欢采用片段式写作方式。体系对应着空洞的超验性。一个体系的建构本身,假如没有谎言的参与将是难以想象的,那么碎片则意味着谎言的反面——一种真实的可能。同时,将激情挤压进正匆忙奔向句号的句子里,显然意味着巨大爆发力的形成,其中每个文字似乎都携带着两个大气压,它们跃跃欲试等待着爆炸。想想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的演讲吧,从语气高亢到声嘶力竭,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换言之,和庞大的哲学体系相比,片段更能保存齐奥朗极为珍视的存在之激情。片段式写作其实早有自己的传统,帕斯卡、拉罗什福科,以及齐奥朗喜欢的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尼采、维特根斯坦等,都曾以片段式札记来记录自己瞬间飞逝的思想。这些学者构成了一种新的哲学:个人化的、警句格言式的、抒情性的、反体系化的哲学,他们正是踩着业已崩溃的哲学体系的瓦砾走过来的。自然,以尼采为代表的这批哲学家是齐奥朗的来源,他们对哲学和信仰的鄙夷,他们恶狠狠的、极端的语气都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桑塔格甚至说:“尼采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写下了齐奥朗几乎所有的观点。”桑塔格并没有就此抨击齐奥朗的“重复”,而是对他“论述更厚重,推敲更精确,修辞更丰富”的表述予以褒扬。
在我看来,齐奥朗之所以在阐述那些猛烈然而并不新鲜的观点时仍旧独具魅力,是因为他对于现代诗歌的借重。片段式写作不仅仅是哲学家的专利,从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直至20世纪的瓦雷里、夏尔等,都是片段式写作的行家里手。有时候,这些诗人笔下的片段被便利地命名为散文诗。这正是齐奥朗另一个来源。齐奥朗著作中对于诗歌的直率赞美不在少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行文风格离诗歌的方式更为接近,这突出表现在齐奥朗文章里逻辑链条的松散:词语处于孤悬状态,它们疯长的触手胡乱捕捉着飘浮在空中的偶然的意义。最终,这些朦胧的句子使意义在摇摆不定中得到增值。对于来自诗人的致命影响,齐奥朗自己有着诗意的表述:“在跟他(指真正的诗人)交往中,在长期生活在他的作品深处之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会发生变化;与其说是我的爱好或是品味,倒不如说是我的血液本身,就仿佛有某种微妙的病症潜入其中,改变了流程、浓度、质量。”这位诗人是谁呢?“雪莱、波德莱尔、里尔克”,他们“在我们身体最深刻的地方起作用,我们会像吸纳一种恶习一样,把他们吸纳进我们自己”。在齐奥朗晚年出版的《笔记选》中,他以奇特的冷漠的方式再次表达了对波德莱尔的敬意:“波德莱尔——我已经有许多年没读他了,他并不是我常常想到的人。”在笔记本上郑重其事地记下对一个诗人的忽视,没有比这更高级的赞美了。其中隐含的反讽正是波德莱尔的拿手好戏,我们可以就此恭喜齐奥朗——他可以出师了。
图说:E.M.Coiran Précis de décomposition
读齐奥朗的文章,我常有恍惚间来到波德莱尔作品后台的感觉,齐奥朗作品中许多疯狂的段落像是出自波德莱尔所描述的那些怪诞人物之口。那个吓走了漂亮小孩的老妇人,那个向驴子致敬的讨好者,身背巨兽没入天际的旅者,以老鼠为玩物的穷孩子等等,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致力于对这些怪人的外部描摹,而齐奥朗则好像是在试图让这些人直接开口说话,如果说波德莱尔还以场景为外衣让这些人依附其中,齐奥朗的文章则完全是赤裸裸关于恶的诉说—甚至称不上是控诉。对于视觉场景描述的弃绝,早就是齐奥朗的自觉行为。在1937年出版的《眼泪与圣徒》一书中,齐奥朗对自己完全转向自省有过辩护:“眼睛的视野有限:它总是从外部观看。然而一旦将世界纳入心中,内省就会是唯一的认知模式。心的视觉空间=上帝+世界+虚无。那就是一切。”当然,诗人对此未必认同。波德莱尔、兰波等诗人习惯于从外部场景的描述入手,并不是他们浅薄或者受到视野的蒙蔽,而是他们对于卡尔·克劳斯的名言——“越是表面的越是深刻”——心领神会。不管怎么说,齐奥朗的决绝毕竟帮助了他,他的固执将他的自省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推进到思想的尽头,在那里在完全的自我意识中,人们倒是有可能重新获得恩典与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