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荒人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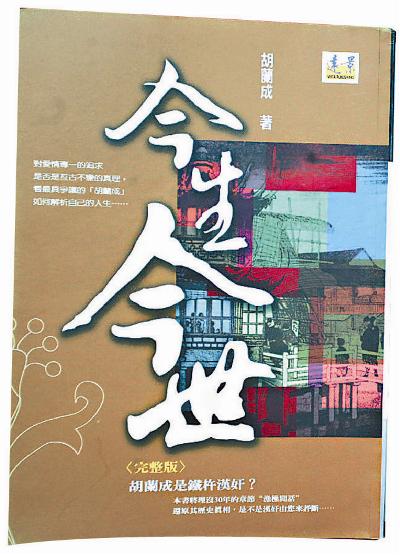
像七月鸣蝉,吱吱不停,也像拔掉的蛀牙,仍隐隐作疼。这真是张爱玲没错,她形容两个心生嫌隙依然共枕的人,心中绝望危疑:「下大雨了,下得那么持久,一片沙沙声,简直是从地面上往上长,黑暗中遍地丛生着琉璃树,微白的蓬蒿,雨的森林。」去温州探视逃亡中的胡兰成,惊觉他除小周(小康)外,另有新欢秀美(巧玉),自己全无立足之地,一夜难眠:「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2009年张爱玲《小团圆》出版,在胡兰成写成《今生今世》(1959)五十年后,这本「今生今世不团圆」狠狠将了他一军。
迟来的复仇,仍是复仇
迟来的复仇,仍是复仇。果真是「full of shocks」,就在1996年朱天文五万字《花忆前身》后,张爱玲《小团圆》也首度打破沉默,十八万字来谈胡兰成。胡兰成写风流自赏的回忆散文,张爱玲藉小说之笔怨毒着书,这桃花女与周公的比试,果然势均力敌,同称精采。《小团圆》写于张爱玲七○年代中期(与〈色.戒〉同时),自传已不足以形容它的真实,笔触之坦露,也完全超越以往。〈色.戒〉里的王佳芝与老易是否为张胡翻版,此书一出,看来是不必争议了,那就是听来的间谍故事,加上张胡恋情的内里。而李黎《浮花飞絮张爱玲》里吹皱一池春水的姪女青芸,看来角色并没有那么单纯。第一次在邵之雍上海住宅见到秀男,「俏丽白净的方圆脸,微鬈的长头发披在肩上,」九莉心里想:「她爱他叔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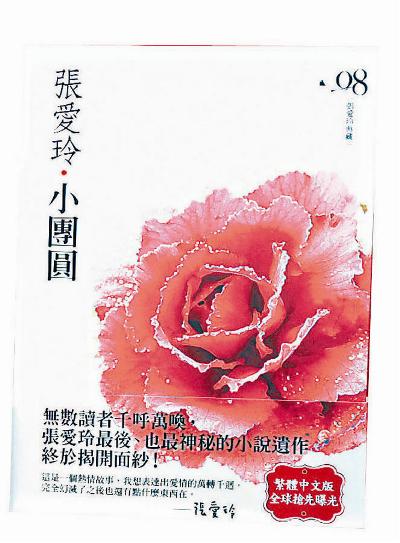
张爱玲处处有这样的灵通剔透,但她待人接物上惊人的愚笨,却教胡兰成很快察觉了。惯于风月的情场浪子,在童女面前,自始至终都是负她的,因之成就了这样一部衔怨负气,「不团圆」的《小团圆》。《小团圆》中的胡兰成形象,果然和带着崇慕胡兰成心态拍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完全不同。这男人风月惯经,善于撩拨,在
b众女之间周旋,床笫之间的大胆,令人咋舌。「像千年狐狸化作白衣秀士,想的是用女子的鲜血供养自己的狐身」,王孝廉〈山河岁月──浅论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说得虽然有些夭寿,可也真是入木三分。
这部古物出土,震动华文世界,被张小虹称为法律上「合法」,情感道义上「盗版」的张爱玲遗作,文字品质毫不逊于她其他作品,话题性更是十足(几乎所有剧中人都可与张爱玲真实人生对得严丝合缝)。前半看来的确人物众多,情节纷乱,与全书主题有点脱钩,尤其与后面的故事主线没有明显的承接。张爱玲修修改改多年,也一直在是否出版间犹豫,看起来像是还没改得满意,倒不是放弃了。她对修改自己的作品,向来极有耐心,像1971年水晶访问她时她自己说的:「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自己欠下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顽强)的。」
才子佳人的变调版
《小团圆》,这个反讽的故事,是才子佳人变调版,三妻四妾不但没有貌美和顺,且不心甘情愿。对张爱玲而言,有不得不写的内在理由,因为欠自己的债,这和她其他作品写作缘由事实上并无二致。酝酿很久,真正动笔是因为听说朱西甯想写她的传记,张爱玲于是有了不如自己写的念头。所以基本上《小团圆》就是以小说形式(人名虚构)写的第一手传记。张爱玲在1976年给宋淇的信上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小团圆》中乱世鸳鸯邵之雍和盛九莉,就像〈色.戒〉里相濡以沫的老易和王佳芝,也像《半生缘》里「再也回不去了」的世钧与曼桢,人生是虚幻的,换了角色名,内里还是同样的那个人。在当事人(张、胡,甚至保管遗物的宋淇)都仙逝了的今日,《小团圆》倒真的可以平心静气当作一个热情故事,而不是隔海叫阵,互相爆料的男女官司来看了。爱情与写作,同样基于一种内在放光的狂热与激越,像张爱玲对水晶说的,她写作的时候,简直是「狂喜」。从万转千回到完全幻灭,其中曲折,正是万千作家写之不尽的。
在目前已经开发殆尽的张学研究外,胡兰成传记、选集及周边史料近年也逐渐被两岸重视。他艺术上的才分无疑是可观的,但为人与气性则完全与张爱玲相背。两人的短暂情缘、未明身分(一纸无效的婚书),就像战时的上海文坛,乱世中开出一朵虚妄之花,虽则灿烂,却极短暂,正如柯灵所说:「过了这村,没了那店」,注定没有结局。
张爱玲示弱,沉默,低调不见人,晚年甚至算得上是人群恐慌症。刘大任形容她是「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郭松棻形容她过马路像一片叶子被吹过对街,在戴文采眼中,她大约只有八十磅,倒垃圾时「弯腰的姿势很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陈少聪担任她的助理,两人演了一年只写纸条避不见面的默剧。然而张爱玲内里的顽强,对人事感知的敏锐与痛苦,完全是一个天才者。这一点,胡兰成在二人初识时写〈论张爱玲〉(1944)就已经充分知觉了。张胡二人的相遇,情感姑且不论,对胡兰成的人生态度与文学表现,是一极大的转折。除了思想理论体系的解散之外,张爱玲以一个天才者接近直观感悟的看世界方式,大大启发了胡兰成在政论之外抒情文字的可能。这从胡后来写成《今生今世》,并称「一炷香想念爱玲,是她开了我的聪明」,略可得知。
【张瑞芬】情感的纯粹与喜悦,对张爱玲而言具有绝对向内性,但胡兰成不是,他对人情、学问、前程、政治都有野心。1944年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婚书后去武汉,名为办《大楚报》,事实上是应日本宇垣一成大将之请,前往筹办一军事政治学校,计画成立军政府。1945年初,汪精卫病逝日本,八月日本投降,据完整版《今生今世》(三三,1990版)〈汉皋解珮〉所记:「我遂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拥兵数万,拒绝(按:重庆政府)接收」。胡兰成的壮志毁于一场突来的急病与邹平凡的转向,武汉只独立了十三日,在全国缉捕汉奸之下,胡兰成亡命出逃。这就是《小团圆》里写的,「楚娣(按:与张同住的姑姑张茂渊)悄悄地笑道:『邵之雍像要作皇帝的样子』」的因由。九莉(张爱玲)不至于认为这事可能成真,她只期望这仗能永远打下去,逃避那终究要来的变局。
当年可能与《今生今世》
打对台
《小团圆》作为《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事隔三十年心情沉淀后才写,当时张爱玲一人独居洛杉几(第二任丈夫赖雅已去世),文字中明显少了爱悦,多了悲凉。将两本书比并来看,可知其中细节真实性相当高,所不同者只是两造的心情差异。胡兰成在情感上的浮滥,以及他带给张爱玲的极大伤害,被张爱玲《小团圆》中九莉一句话说尽了:「我不能和半个人类为敌。」另一个被害的护士小康(小周)的版本,则是泪眼哭倒(胡逃亡前硬要了她的身子):「我可怎么办,他是有太太的。」只是这「太太」,也不是九莉(张爱玲)。
从政治立场到情感态度,胡兰成都有着一贯的超验性。他自比为刘邦或国父,自称为「浪子」,能「无端欢喜,惊险亦如惊艳,无因无由忽又有了办法,故不堕劫数」。1964年写于日本的〈反省篇〉中,可看出胡兰成始终以「亡命」自居(不承认现在的权力,不服罪),他是要创建新秩序,因此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之感。早在温州避难时期,背负着各方汉奸指责,他就有这样的文学与人生观。在《苦竹》上,他说:「我写,只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并不为了什么。我想革命也一样,有人可以作了错事,仍然不是罪恶的,也有人作了好事,而仍然不伟大。」他又极端爱悦青春鲜洁,别有一种性别反串和乔装作致的意态,一种宛若天山童姥般的童颜稚语。美若天仙,却像罂粟花般,暗藏杀机。
《小团圆》写尽全天下痴情女的天真(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是有老婆的),也把一个最理直气壮的负心汉写活了(妳这样痛苦也是好的)。《今生今世》文字跌宕生姿,婉媚至极,其实是胡兰成历数一生情人的群芳谱,聚碑成塔,「采四海花,酿天下酒」,张爱玲只落得一个过场,成了「民国女子」这一章的材料。
胡兰成《今生今世》成书于1959年日本,当时生活初定,已与佘爱珍结婚,这本半自传散文充满风流自喜,顾盼自得,没有半点忏悔或救赎的意味,胡甚且寄了此书给在美国的张爱玲,顺便撩拨她。张爱玲看完的感受无人知道,现在《小团圆》出版,终于揭开了这「憎笑得要叫起来」的谜底。
「九莉想道:『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就知道保存他所有的』。」
她没往下说,之雍便道:「妳能这样痛苦也是好的。」
是说她能有这样强烈的感情是好的。又是他那一套,「好的」与「不好的」。使她憎笑得要叫起来。
张爱玲之于人生,采冷眼静观的姿态,总在那阴暗处窥视着,而胡兰成则永远意识着自我的存在,兴高采烈地活着。我们从二人惯用的意象,亦可看出其间本质上的差别。张爱玲尚「月亮」的阴暗,她那「蓝阴阴的月光」,「有着静静的杀机」,或「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明月」,「像个戏剧化的狰狞脸谱」。而胡兰成《今生今世》的阳光处处,适与之形成对比。例如:「好男如阳光,好女如颜色」,「十里桑地秧田,日影沙堤,就像脚下的地都是黄金铺的」,「桃花极艳,但那颜色即是阳光」,「是一种可与阳光游戏的颜色」,「记得是下午,屋瓦上都是阳光」。只是这阳光男风流自赏的背后,胡兰成可不知道在逃亡前夕两人燕好时,他还对武汉小周恋恋难舍,张爱玲《小团圆》里是这样写她的决绝的:
「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把切西瓜的长刀,比较伏手。对准了那狭窄的金色背脊一刀。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拖下楼梯往街上一丢。看秀男(按:姪女青芸)有什么办法。」
在给宋淇的信中,张爱玲甚且认为,还好当年写给胡兰成的信全要回来了,「不然早出土了」。如今想来,宋淇是个实心眼的益友,当年的决断可能是对的,七○年代中期《小团圆》若在台湾出版,刚好与胡兰成重版的《今生今世》打对台,当时张爱玲声誉鹊起,并不如现在这么地位崇隆,不可移易。且不说胡兰成可能有的私心,世人当如何看待这各说各话的男女官司?
「时间是不可逆的,生命是不可逆的,然则书写的时候,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六十年前的情书与六十年后的复仇都不嫌晚,《小团圆》证明了张爱玲的耐心,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的。
原载《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