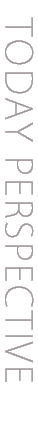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顾颉刚与谭慕愚──一段缠绵了五十年的情缘
余英时
顾先生真是情痴,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在谭七月二十七日曰去西北之前,他又赶着做出一次巨大的努力。七月二十五日记:
到典试会,抄致健常函四千字。此函凡一万三千字。
这是比上次万言更长的一封信,所费心血和时间可想而知。七月二十六日:
将致健常书复看一遍,出,打长途电话与健常,则已行矣。
今日欲将致健常信寄出,而不知其何在,因打电话到内政部,则渠于今早进城矣。及晤镜吾,知数日前渠自城回部,车经歌乐山,仅下车与彼一谈,谓“事太忙,顾先生处不能去,以后通信罢!”镜吾知其飞机期为二十七,则今日进城便径赴西北矣。渠事固忙,然三次经歌乐山而不一来,又不寄一信,其有取瑟而歌之意耶?若然,则予既丧贤妻,复失良友,倒霉透顶矣!为此,下午及晚间均不能眠。
七月三十一日才得到关于慕愚出行的确切消息:
镜吾告我,渠前日进城,至曹孟君处,知健常飞机票都未买得,公司中嘱其于廿七日至站上待,是日孟君未送而彼亦未归,则即于彼日行矣。渠此行绝不告我,一个人倒霉时真无处不倒霉也。
这样看来,他那一万三千字的长信连寄出去的机会也没有。日记中连呼“倒霉”,即是承认“伉俪”与“朋友”已两俱失矣。
谭慕愚此行为期数月,踪迹不定,但顾先生仍未能忘情,还是随时注意她的动向,十月九日:
接九月廿二日张令琦来书,知健常已访其父鸿汀先生。
十月十日:
本日《大公报》载健常本月四日偕高一涵到西宁,九日回兰州,想见此行匆匆之状。甘、青、宁三省既俱到,谅本月内即回渝矣。
但他此时已从幻梦中醒来,再过三天(十月十三日)他便接受朋友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了。(丁长叹)一九四四年五月九日,与张静秋订婚一个月以后,顾先生写了下面一段日记:
与静秋同到宿舍整理衣服。出前数年日记及去年致健常书与同读,并谈论其事,直至五时。(丁为之挢舌)
与静秋续谈健常,直至十时。(丁按:顾先生为人坦荡啊)
静秋观予向健常求婚书,颇指摘其无情,又谓如此用情纯厚者能有几人。晚衔晋来,谓健常怂恿其妹打胎,且屡函其妹骂衔晋,挑拨其夫妻感情,前年内政部出一科员缺,又强迫衔晋往任之,天天寄快信。此等事皆不合情理,而出之于我挚爱之健常,真刺伤我心。因太兴奋,晚遂失眠,以无水,未服药。(丁按:喜欢这六个字)
这是第三阶段有关谭慕愚的最后一条日记,大概是向未婚妻详细交待他和谭的关系,所以谈得这样久。谭的拒婚无疑是顾先生一生在感情上受到的最大创伤,短期内很难平复。正是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谭的妹夫(衔晋)对她的种种指摘,他才会照单全收。日记中“真刺伤我心”五个字其实只有用在拒婚事上才铢两悉称。
顾、谭的故事在这部《日记》中占有很中心的位置,故事本身的发展也使读者不断发生新的期待,然而它竟戛然而止,结束得教人泄气。这时一个典型的反高潮(anticlimax)。
在谭慕愚方面的资料完全缺席的情况下,故事只能就此落幕。故事结束了,然而还有余波荡漾,这是中国大陆天翻地覆以后的事,仍值得一记。
《日记》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
览报悉健常在京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此次被派赴苏,为五一节观礼团员,长风万里,殊可羡。念五卅惨案时,渠为国家主义派,反共最烈,刘尊一为共产党,常与齕。其后刘被潘宜之逼为妾媵,堕落为富家妇,(丁按:惊出一身冷汗。谨记此诫)而渠一意奋斗,乃有今日之长征。世事变幻,宛然一梦也!
顾先生偶然在报上发现谭被派赴苏联的新闻,不胜惊讶和感慨,因此留下了这条日记。他惊讶的是当年“反共最烈”的人竟能获此殊荣,而同时与谭正面斗争的共产党员刘尊一却已没落无闻了。谭、刘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与顾初次同游颐和园的北大女生中之二人,在学生运动中分别是右派与左派的领军人物。但一九五一年时两人的升沉荣辱却与当年的政治立场完全颠倒了。难怪他要发出“世事变幻,宛然一梦”的感慨了。
其实在顾先生写这条日记的时候,刘尊一(一九O四—一九七九)已不再是“富家妇”,她在西南师范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的职位,与吴宓同事。吴宓对她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
年四十七岁,初嫁何,生一子。先在北大从李大钊游,遂入共党,同任要职。一九二七夫妇在沪被捕,何死;再嫁桂人潘宜之,生二子二女。约八年前,潘遇刺死。近其仇每以“双失节”讥之云。
《吴宓日记续编》有关刘的记述不少,因与此处的讨论无关,从略。无论如何,刘已边缘化,与谭之显赫不同,确是无可否认的。谭在此时何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待遇,必须另作研究,不过我愿意提供一个可能的推测。我记得一九四九年秋黄绍竑是国民党的和平代表之一;他在北平还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词。开首是“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谭慕愚追随黄二十年,或即是当时随员之一。……派谭去莫斯科恰好可以昭示国民党及其他反共的团体和个人:像谭慕愚这样当年“反共最烈”的人都可以受到重用,你们还怕什么呢?(丁按:政治最龌龊最无趣)姑至于此,以待将来验证。
一九五四年顾北行以后,与谭仍免不了在公共场合会面。这是因为顾的政治单位是“民主促进会”,谭则属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而两人分别在政协与人大。我在《日记》中只发现一条谭请顾午饭的记录。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到惕吾处,(丁按:“惕吾”是谭慕愚一九三O年以后的正式姓名,前已述及。可叹孤先生再不以“健常”称之)长谈,留饭。
今午同席:曾萍、王伟、黄镜吾、谭家昆及其子女(以上客)。谭惕吾及其子利民、女静(以上主)。惕吾之母已于去年在京逝世。其子女二人则所抚孤儿也。
这时拜年而留下午饭并作长谈,距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拒婚之会已十二年了。谭始终不结婚,抚孤以代子女,可知她或早已抱独身主义。两人这次谈些什么,日记一字未提,甚为可惜。但这次相见之后,顾的旧情又有复发的迹象。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
静秋加入妇女联谊会,今日会中同人到北海游玩,因邀同去。
在北海休树下,杨花扑面,忽起感伤,因改前人诗数字以抒予怀:
风光渐老见春羞,到处凝情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乱飞烟絮上人头。
轻红桥上立逡巡,渌水微波渐作鳞,手拈柳丝(丁按:柳丝!快给我磕头!)无一语,卅年春恨细如尘。
噫,放翁行作稽山土时,尚感沈园之柳棉,况予耶!
三十年前是一九二五年,正是他和谭慕愚常常同游北海的岁月。放翁“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之句此时亦必往来胸中,不能自已。若更推之二十三年后(一九七八)题《日记》所写“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之诗,那就和放翁“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棉”的心境完全合一了。
顾先生自初识谭慕愚,便为她的“勇猛精进”所折服,后来又一再称许她“有良心、有志气、有魄力、有眼光、有胆量”等等。他又说她“频遭夜行者之按剑,世无真知,我自喜为九方皋矣”。就此点而言,他确不愧为谭慕愚的知己。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在谭的晚年又有了一次最痛快淋漓的发挥。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顾先生在《日记》中告诉我们:
报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女生林希翎(亦名程海果)大发反社会主义谬论,渠曾住谭惕吾家,与黄绍竑亦有往还。予前览报,觉民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有组织,有阴谋,(丁按:呃……好像不至于……只是说话太随便……)而民革若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不过说话随便,(丁按:……)似不当同等看待。今观人大揭发,殆不其然。论世知人,戛戛乎难哉!
谭惕吾变成“右派”足证她仍然坚持着早年的某些理想,不可与随波逐流的“靠拢分子”相提并论。林希翎既曾在她家中住过一段时期,思想上的影响大概也不能完全避免,具体的情况,希望将来有人能发掘出来。我写这篇文字时,没有时间去追踪谭一方面的资料,是一憾事,但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发现沈从文先生有一段对她的描述,恰好发生在她打成“右派”之后,姑且引在这里作为参考。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沈在青岛《致张兆和》中说:
耀平的上司林**果然已露头角。这人和我在上海一处视察,样子就张扬不本分,不像个有学问的人,相反和个上海商人差不多。正如谭惕吾,给我印象即不好,一看就像个只想兴风作浪小政客,又没有什么知识本领,我还奇怪怎么这些人都是人民代表?
信中提到的林某一定也是“右派”,故称之为“已露头角”。沈先生是一位谨慎本分的人,(丁re)一生不沾政治,因此与林、谭两人都气味不相投,对他们印象很不好。但他用“兴风作浪”四字形容谭惕吾,却值得注意。这就表示谭对当时政治很不满意,平时一定流露出不少批评的意见。(丁按:嗯……除了顾先生的一往情深外,其他人对谭的评价都不高。最引人之处,在谭慕愚一单身女子,于政坛沉浮经营数十年,本身就是少见的近代妇女史个案,值得研究)最使我动容的是顾先生一九五八年四月尾的一条日记:
本月(按:四月)十八日到社会主义学院参观大字报,诸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李健生、黄绍竑、储安平、费孝通、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叶恭绰咸有,独不见龙云、章乃器、谭惕吾三人,盖彼辈不肯学习也。与伯昕谈,我辈要否去劝一劝。渠云不必,统战部曾召集右派分子开会劝导,谭惕吾发言仍强硬不服罪,毛主席说,让他们待着看罢。(丁按:这句话我要设为签名档)闻之殊为忧虑,今日何日,乃犹作死硬派耶!龙云年老不必说,章乃器、谭惕吾年均五十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可作为,乃将以死硬派终耶?……闻章乃器之妻杨美贞虽亦划为右派分子,但已与其夫分居,临别之际,章乃器斥之为“卖夫求荣”。(丁哭)
打成“右派”一年之后仍然不肯屈服、拒绝“学习”的只剩下三个人,谭即其中之一,她的志气、良心、气魄……已显露无遗。更出人意表的是,在统战部集会劝导的场合,谭慕愚发言“仍强硬不服罪”,……这已不是“勇猛”、“胆量”所能形容其万一。孟子所为“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和庄子所谓“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庶几近之。
顾先生相去劝她,可见关怀之情不减往昔。但是他们两人此时的思想距离,相去已甚远。谭负隅顽抗之际正值顾“向党交心”之时。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的《自我改造大跃进快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出版)上登出了下面的记载:
不少领导同志在竞赛中一再挑战加码。中委顾颉刚同志原交二百条,但他在翻阅自己解放头两年的日记后,感到要说的心里话很多,就主动提出增加指标到五百七十条,向杨东莼、严景耀同志和原来指标最高的陈慧同志挑战,陈慧同志以二百八十条应战。不仅比数量,还要比深、比透。(见《日记》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条末)(丁按:这些内容,可单独列为“解放后”一章,直接跳过不读,以免伤心)
……《日记》后来还有两次提到谭: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
予打电话与健常,未通,岂真有憾于我耶,抑他迁耶,今生尚得相见耶?思之怅然。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今日报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法制委员会,费孝通、谭惕吾皆在,知一九五七年之冤狱一洗而空矣。为之喜慰。
顾先生情有独钟,终身不忘,古今少见。但是从一九五八年起,他和谭慕愚已各自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明确的选择,“君向潇湘我向秦”,这是无可奈何的人间恨事,然而这应该怪谁呢?
原载:《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余英时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3月出版)
(一) (二) (三)(四)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