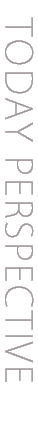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一本书的最深处:读者与作者的对话
韩少功/季亚娅
多义的乡村之乡村伦理
季亚娅:下面我把《鸟巢》《守灵人》《中国式礼拜》这三篇文章放在一起来谈。这其中,《鸟巢》是从动物生态学来看人的伦理观的形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生物界的普通规律。《守灵人》谈中国人的祖宗观念。《中国式礼拜》谈到传统乡村中国的伦理约束机制。中国人认同祖宗和西方人认同上帝相类似。您说:一旦祭祖的鞭炮声不再响起,那寂静会透露出更多的不祥。这里的思想方法其实和上文所说的类似,就是我们在这种亲历中非常贴心贴肺地理解了这些东西。
韩少功:什么叫传统?什么叫文化?这些就是。欧洲人承接游牧传统,把一个亲人埋在这里,其余亲人就走了,赶着马车到别处寻找水源和牧草。所以他们对祖先不会有我们这样强烈的感情和意识,也不大讲究“游子悲乡”、“落叶归根”。我在书中用了一个词:定居。定居者生活在祖先的包围之中,很容易产生一种特殊文化。祖先天天盯着你,你能肆无忌惮地伤天害理吗?中国人,主要是汉区人,没有发育出西方的那种宗教,而是所谓“慎终追远”,建立了祖先崇拜,祖先与神鬼多位一体,构成了最重要的约束机制。做事要对得起祖宗。自己挨骂不要紧,祖宗挨骂则万万不能,一定动刀见血。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这么来的。
季亚娅:类似的篇目还有《一师教》。为什么宗教会在农村盛行?您分析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是一杆“公平秤”,还因为生病了可以不求医与躲避人情债。这些合情合理的分析,源自对一种最底层生活的了解与贴心贴肺的描摹。
韩少功:一个东西的产生总有它的道理。教条主义者最喜欢想当然,不去深究和体察实际生活中隐藏的道理。
季亚娅:这是教条主义者的不见,他根本看不见这些东西。
韩少功:现在医药费居高不下,传教者说入教可以百病自消,肯定会有吸引力。当然,其他原因也不可忽视。比如大家心灵无依,灵魂空虚,人际关系冷漠,需要找到一个寄托,需要某种归宿感和团体的安慰,这也会促进宗教的发展。
季亚娅:下面一组牵涉到乡村自己的运行逻辑:《老逃同志》讲述的是乡村生活的义道,全村人给客居的逃兵养老送终。《垃圾户》讲述的是狡猾与信用不可思议的结合:某困难户不惜胡搅蛮缠盖一个较为便宜的房子竟是为了省下钱还赌债。他竟会把还不还赌债的信义看得比房子重要,为此不惜得罪所有帮他盖房的人。如何理解这种价值标准的轻重之分?
韩少功:人都是丰富的存在。一个小人物,哪怕是一个庸人,甚至一个坏人,都未见得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坏亲戚,不见得是一个坏邻居。一个坏领导,不见得是一个坏父亲。这种五花八门的多面体因人而异。一个合格的作家,看事物起码应该比常人更看到多一点,哪怕多不了多少。
季亚娅:义道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结合生活方式来分析?
韩少功: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人特别容易一盘散沙,但有些奇怪的是,中国人又是人情味特别浓的群体。比方几个中国哥们儿一起聚餐,可能都抢着买单。但欧美人会非常习惯于AA制。但是中国人又特别擅长窝里斗,三个和尚没水喝,不像欧美人那样擅长于建立组织与制度。这是一种特别复杂的文化心理状态。如果我们要讨论国民性的话,与其谈谈阿Q,还不如谈谈这些东西。这里面隐藏了很多中国特有的文化基因。
像《逃兵》里的情况,一个无人照顾的孤老,在西方只能交给教会组织或者社会福利机构。但中国在没有类似福利机构以前,只能靠民间传统来解决问题。这种传统在从前经常表现为祠堂制度、会馆制度等等。比方我是湘潭县的,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遇到困难了,就找那里的湘潭会馆,求得一些帮助。如果有人考上大学了,又没有钱上学,那他也可以求助于宗族,等着祠堂里开会议事,各家各户都伸一把手,凑钱让穷孩子读大学。
季亚娅:很多书里提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之后这些东西消失了。
韩少功:消失了,因为我们按照西方的眼光,只承认国家、党团、工会、教会这一类组织是合法的,而会馆这一类地方组织、祠堂这一类宗族组织是不合法的。其实,很多农民并不习惯西方式的组织,比方孩子没钱读书了,不会去找党团和教会,还是去找同姓的各位宗亲。这样,简单地说中国农民缺乏组织能力是不公平的,是强压着一群鸡做鸭叫,然后责难它叫得不像。要知道,中国以前某些会馆、祠堂、行帮、票号等等,也曾组织得极其严密和效率惊人。这些组织不是没有弊端,中国人建立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也确实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我们应该用辩证法的态度,平实看待合理中的不合理,不合理中的合理。
季亚娅:下面一个问题是《面子》,这个很好玩。
韩少功:我这本书里其实很多问题都牵涉到怎么认识中国的民间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有点像田野调查。《面子》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好面子,面子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面子原来外国人翻译成尊严,后来他们也觉得不对。现在我看到有的西方文本干脆用音译,叫做“mianzi”(二人笑)。
季亚娅:《欢乐之路》有一个非常生动的细节。村里的三明爹病得快死了,一听说修路捐了一千元钱,理由居然是修好了路他可以在阴间向早就修通了公路的两位亲家炫耀。这要放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一定会把这样的原因隐去,大力宣传其美德。
韩少功:面子是中国人的重要精神文化元素,经常比钱财还重要。有些经济学家说,人性的核心铁律就是利益最大化。我对这一点略有保留,至少认为它不够全面。宗教徒就算不上利益最大化,是心灵慰藉最大化吧?小孩子也算不上利益最大化,是好玩最大化吧?还有一些农民盖那些不实惠和不合用的小洋宅,不过是面子最大化,倒是让自己的不方便最大化了。当然你可以说,面子也是利益的一部分。但是这里的利益观取决于特定文化制约:在一种文化里面,这种事是有面子的,但在另一种文化中,这种事恰好是没面子的。所以铁律不铁,因文化而变。如果经济学把利益最大化当作铁律,就很可能要犯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错误。
多义的乡村之农村工作指南
季亚娅:接下来是某一类特殊的农村题材文章,它们是《开会》《非典时期》《非法法也》《气死屈原》《兵荒马乱》《各种抗税理由》,和上一类田野调查式的作品明显不同。它们应该来自农村基层工作者的最实际具体的日常工作经验。我会把它们和赵树理的“农村工作指南”的那一类小说相比较。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同时期里,最为了解中国农村以及农民心理的作家恐怕就数你们二人。
我的毕业论文答辩时,有老师问到“知人论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举了《开会》的例子。如何禁码在我们看来这个没办法解决的难题,贺乡长用了一个在农村的价值观里比天大的理由——您不能骂我娘,轻轻松松占据了道德优势,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对于这一类的书写我非常感慨。赵树理的写作有很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是要给人当成“农村实际工作指南”。您的创作意图呢?您同意这个判断吗?
韩少功:我对赵树理的作品读得不全,也不赞成作家自居老师,把写小说当作写教材。但做社会工作要了解人,与作家了解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从政者要懂一点心理学和文化学,与作家们的知识结构也会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有些读书人下乡,对农民只会讲大道理,讲正道理,经常是讲不通的。有时候小道理比大道理管用,歪道理比正道理管用。我发现能干的农民或者乡村干部都有这个普遍特点:善于讲歪理,只是歪理并不全歪,实际上是歪中有正,隐含和运用着一些重大的潜规则。比方说,那个贺乡长不讲政策讲母亲,迅速掌握话语优势,就是巧妙利用了中国农民的孝道,利用了中国农民的某种思维定势——这还不是天大的道理?
季亚娅:还有《非典时期》,非典时期乡人放鞭炮祭瘟神,理由是礼多人不怪,贺乡长号召大家讲科学:“你要是命里有不放也没事,你要是命里无,放再多鞭炮顶个卵用。”乡长的这番科学道理很让农民信服。这和开会那篇有点像,都可以看成是农村工作手册的。只是因为你本身的学养以及对于整个时代的清醒判断乃至作家中少有的世界史眼光,使这种理解与温情中透露出另一种思辨的清冷味道。
《非法法也》讲到的是法律之外的天理人情。有人偷剪电线导致二人在水田触电而死。但贺乡长找供电公司做替罪羊,争取高额赔偿,理由是既可挽救死者的家庭,又避免了第三个家庭的崩溃。法理大不过人情!如此通达狡黠又智慧,哪里是书呆子想得到的。还有《气死屈原》《兵荒马乱》《各种抗税理由》等等。
韩少功:西方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以后,会产生一些排异现象,很多本土潜规则并不会立即退出历史。我翻《宋史》和《明史》的时候,发现中国古代法律非常有意思,比方说“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当官的可自动免罪,而是说死罪也不杀你,让你去自杀,以免坏了君臣之礼。又比方说亲人作伪证,当然是罪,但可以免刑,因为亲人不作伪证,那还有人味吗?还谈什么孝悌之礼?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是在法律与人情之间尽可能平衡与调适,与西方的法制大为异趣。
季亚娅:但我们经常在一些小说里看到相反的描述,大义灭亲。例如您写过一篇小说叫《兄弟》讲述父亲举报儿子的悲剧性故事。
韩少功:现代中国人不讲宋律和明律了嘛,不讲孔子了嘛。孔子在《论语》里说过:有人偷了羊,儿子去举报他,这在你们看来是正直,在我们那儿就不一样,有人偷了羊,儿子替他隐瞒,这才是我们的正直。在孔子看来,如果亲人不包庇亲人,那还像话吗?
《老地主》一章里有一句话:新派人物往往注重理论和政策,但是农民不一样,更愿意记住一些细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思维方式差不多是文学的方式。农民擅长直观,擅长形象记忆,擅长以日常的言行细节来判断人物。而且他们为什么不大习惯理论与政策?因为理论和政策很容易把生活简单化,比如用私田数量标准来一刀切,划定“地主”或“富农”——这在农民看来就太简单了。农民在判断人物时几乎都有文学家的眼光。
多义的乡村之农村现实问题
季亚娅:接下来是《口碑之疑》。它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修路带给村人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这个似乎正是现代化两面性的隐喻?我记得您在汨罗乡干部的培训班上曾经讲过。
韩少功:辩证法是中国人的一碗饭,男女老少都会用,甚至用得不露痕迹,比如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坏事变好事”、“塞翁失马”、“因祸得福”等等,这种成语和俗语比比皆是。
季亚娅:这篇文章中第二个问题很好玩,农民期盼自己村的大学生毕业后在财政局、公路局等部门工作,到处都有我们的人。这个说的是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人情伦理社会吗?
韩少功:人情社会的负面效应就是不讲是非,大乱法度。这正是我们现实的一部分。你觉得匪夷所思,但这对于书中的人物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合情合理的,逻辑性很强的。
季亚娅:接下来讲述的是“口碑”的可疑,是历史本身丢失的和隐藏的那些东西。从这个“口碑”的可疑出发,回头我们就会想到历史上的很多判断,也是很可疑的。如果我们不是亲历者,也找不到亲历者,那么是否永远无法知道可疑叙事背后的真相?
韩少功:任何真相都是无法穷知的。所谓了解从来差不多都是一知半解,既取决于史料的有无多少,又取决于我们使用史料的立场与方法。在生态意识强化之前,我们说贞观之治或文景之治,大多都会将其归结为执政者的美德与才智。在生态意识强化之后,我们才会注意到这些大治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人口因战争而大量减少,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大大缓和。这就是不同的眼光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真相。
季亚娅:下一篇讲述的是农村土地问题:《疑似脚印》。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是您应法国某写作协会之邀而写作的,名曰土地,记录下一位失去土地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但后半部分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其实这同一个人是非常愿意离开土地从事别的营生的。现实生活总是以这样复杂的方式在呈现吗?
韩少功:人的感情与理智并不是时时统一。主人公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但在理智层面完全可能背道而驰。这一篇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紧张和对峙。这也是表达作者必要的自疑。
季亚娅:这篇文章中提到农村土地私有化这个现实问题您怎么看,或许这个问题与文学的关系不大,我应该去请教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实问题。
韩少功:文学的价值判断通常是迟到的。文学不需要那么快地对现实做出简单明了的判断,其首要责任要把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认识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而文学比较擅长这个开始,其余的事由理论家来做可能更好。上帝的事交给上帝,恺撒的事交给恺撒。文学最需要做的,是显现生活的多义性。
季亚娅:下面我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我认为它们是结合乡村经验对“科学”这个命题的反思。《船老板》,他把自己的巫术称之为科学。《卫星佬》科学技术的乡村普及版,这一篇非常有意思。虽然您说所有的总结都会遗漏掉一些东西,但有的东西还是会呈现得更清晰。例如科学的神话或者它本身的意识形态。虽然我现在很不愿意用这样的词来表达。
韩少功:科学是这个时代的强势话语,而且在这一个世纪以来逐步进入到乡村,和乡村的诸多细节发生关系。船老板热衷于巫术但喜欢借用科学的名义,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科学的威力多么强大。另一方面,科学的本土化是一个很生动的过程,“卫星”与“杀猪”的结合不过是事例之一。这里是无知,还是智慧?是野蛮的糟蹋,还是天才的创造?确实耐人寻味。
季亚娅:从前有一种赤脚医生制度是否与此类似。
韩少功:那也是科学本土化和本土科学化的一种互动方式。志在普及科学的人最应该了解这些方式。
季亚娅:船老板真用巫术帮主人找回了那只鸡?
韩少功:是真的,我也无法理解。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无法了解的谜,等待未来科学的破解。有些巫术也是这样。据说现在很多老师在考试前让学生大喊三声:我是最棒的,然后再去考试。这种所谓心理暗示,恐怕也是一种现代巫术吧?如果它确实有效,用用也无妨,不必计较老师教唆学生吹牛撒谎。
(一) (二) (三)(四)(五)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