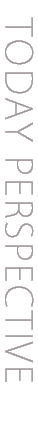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一本书的最深处:读者与作者的对话
韩少功/季亚娅
二、此书之内
季亚娅:好,下面我们来看《山南水北》,这是一本非常好玩的书,有很多来自实际生活的最精妙的智慧。我们都觉得您是很少有的对我们这个时代保持共时状态的作家,或者说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您保持少有的清醒(韩:清醒也不一定好,难得糊涂嘛)。作为一个诚恳的读者,我的阅读方法是将这些文章从内容上进行简单归类,从全书的语境以及您一贯的创作脉络中入手,争取找出文本背后那些“沉默的不曾言说的东西”。下面找找看?我们进入第一篇吧。
从前、传统与回归
季亚娅:第一篇是《扑进画框》,可能是因为“第一”这种编排,我会努力地从中找出理解全书一些线索,也许这种方式本身有问题。这一篇文章我发现了全书的几个主题:文章开篇您写到对八景峒最初的观感“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我感到这船不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
这里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您好像把自己的回归放在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的时空背景里,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归是一个朝向文化传统的游历。是不是有这一点?而且这个传统首先指的是文化中非正统的那一部分,因为你会说:我今天在这里“落草”。我想起《马桥词典》里您描述到罗国的反抗传统,还有九十年代您的散文《人在江湖》里描写到“江湖”这个词与汨罗的关联,您是否再次在强调这些被压抑的或者反抗官方的传统?此文中您提到的第二个传统是劳动的传统:“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于是,我从这两个维度来理解您为什么要回到八景峒,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或者因为它放在第一篇而有所夸大?或者还有其他未曾言说的意义?
韩少功:如果没有这片湖水,我这段议论肯定是不成立的。是这片湖水触发我的想象,这里面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也许这个偶然的后面也有一定的根由,比如对江湖好汉的造反有一种隐秘的向往之情。
季亚娅:就是“不服周”吗?
韩少功:湖南人说的“不服周”是一种挑战精神。张承志说,艺术就是一个人对全社会的挑战。文学家不挑战,简直就是不务正业。
季亚娅:为什么对劳动感兴趣?您这本书还有一组和劳动有关的文章,我挑出来都在这儿说一下:《开荒第一天》您写“坦率地说,我怀念劳动”。《月下狂欢》,“劳动的欢乐完全可以从贫苦中剥离出来”。《欢乐之路》,您写到修路的劳动场景与群体欢乐,“我不愿落入文学的排污管,同一些同行比着在稿纸上排泄,我眼下更愿意转过身去,投身生活中的敞亮与快乐”!还有《认识了华子》写一个好炮手,《也认识了老应》写一个好挖土师傅。这两篇文章您讲的是劳动给人的面子和尊严(韩:对)。特别是《开荒第一天》,您谈到了劳动与知识的关系。您说,“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会不会成为生命实践的局外人和游离者”。而这一点,和《暗示》中以“体”为知识和认识的基础一脉相承。我想请您谈谈劳动与知识的关系,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想法,而这样的想法在今天有什么意义?
韩少功:上帝给了人一个大脑,也给了我们一个躯体,人就是应该劳心和劳力的结合或者说一种平衡。现在社会的这种体制,把人分割成劳动的阶级和不劳动的阶级,或者说,劳动本身又是有等级的,最下等的是体力劳动。虽然这种不公的等级制已经延续了几十个世纪,甚至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现象。但是没法改变是一回事,你觉得它是否合理,是不是有美感,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直认为,一个理想的生活方式应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劳力和劳心的并举。
季亚娅:您这个好像与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社会很类似,和某些乌托邦社会的理想也很相像。
韩少功:对,还有毛泽东时代的学工学农。这个可以另作分析。但劳动确实是我们生存的第一天职。基督教徒当年说:最好的祈祷就是劳动。新教教徒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乘着五月花号海船到达新大陆的时候,都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一个人可以不去求神读经,但不能不劳动。后来的美国人特别爱劳动,干什么都喜欢自己动手,就受这一条影响。这不像中国人,只要有一点小钱,就会尽可能雇用仆人,自己裹小脚,留指甲,穿长袍,都是不便劳动的装束,是贵人和假贵人的时尚。
季亚娅:我总结一下:第一,您是对劳动等级差别中的不公特别反感……
韩少功:这是一方面。第二,劳动有利于增强人的务实态度,这是认识论方面的意义。第三,劳动有利于创造人的生命美学,这是艺术审美方面的意义。您想想,一个小白脸,看起来总是不那么顺眼吧(二人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弱不禁风、哎哎哟哟那一类,我很讨厌。我在文章里面写道:有科学家推测人以后会变得像章鱼一样,有一个大脑然后有很多触须来按电脑键盘就可以了。这不是很可怕吗?何况我们的劳动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我们掩盖了,由其他人来承担了。只是媒体也好,意识形态也好,常常掩盖这种承担(插话:这个说得很好),好像我们成天不干活也可以活得很好。
季亚娅:还有您在书中谈到的劳动的欢乐,可以把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那种欢乐,请您谈谈。
韩少功:最美味的享受其实是在劳动之后,是以劳动为前提的。你看现在有些孩子,当着小皇帝,长大了还是“啃老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幸福吗?肯定不那么幸福,对幸福的感受非常浅,非常稀少。最好的美食,肯定是在饥饿之后。最好的休息,肯定是在劳累之后。而这些幸福是很多吸血虫享受不到的(笑)。
季亚娅:好像是这样。那接下来——我要检讨这种提问方式,好像是我要强调和突出某些方面——《开荒第一天》中写到的“体”与“认”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而且您从前有一篇写墨子的散文,认为墨家的知识是从劳动中得来的。这是否是另一种知识等级的重新建构?劳动中所得来的知识就一定比书本的知识高吗?
韩少功:知识的源头一定在实践之中。异想天开和闭门造车的知识,偶然也有,比方说欧洲有人提到先验论,说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某些元素就是推导出来的,不需要实践。数学上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虚数就是纯逻辑的产物,与物质世界并无对应关系。但这些演绎成功的例证,无不以大量归纳为前提,演绎只是归纳的延伸和衍生,间接知识只是直接知识的延伸和衍生。康德一辈子待在一个小城里,似乎实践范围有限,但他所依托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成果,都是他人在实践中获取的。他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才能向上跳,才能关起门来推导他的理论体系。
季亚娅:还有“华子”和“老应”那两篇,虽然您会用一种幽默反讽的笔调来写他们的“有面子”,但骨子里还是很强调劳动本身带给人的尊严感……
韩少功:对,尊严。那些小人物似乎不值一提,其实他们同样掌握着丰富的知识。只是我们常常在知识中建立等级,以为一个股评家或投资家的知识很高明,而把一个乡间的炮手的知识看得一钱不值。但事情是经常变化的啊,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总韦尔奇来演讲,门票炒到一万块钱一张。但他的公司眼下大亏损,百分之九十的公司亏损,那他的知识还值不值钱?其实,知识的价格并不等于价值,一个炮手的知识并不比一个股评家或投资家的低(二人大笑)。文学家为天地立心,关心恒久的价值而不是一时的价格,因此以平等之心对待天下众生,包括很多小人物那里被人歧视、忽略、掩盖的知识。
季亚娅:下面是《回到从前》,这个标题我觉得可以视为理解全书的关键词。我注意到一句话“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多年以前的那条路”。我想问,这条路是什么?
韩少功:它是乡下那条我们以前经常赤着脚在早上或者夜晚走过的土路。因为在你年轻时经历过它,它就可能在你的心里烙印得非常深……文章中有些句子不一定出于预谋,有时是跟着感觉走,写到哪里算哪里。三个重复的“多年以前”是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的,那就认下吧。
季亚娅:(大笑)其实您知道我问您的是什么,然后您就会告诉我这就是那条乡村的土路。我本来还是给您预备了几个答案的:在2002年法国的一次演讲里,您谈到您是一个逆行者,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里,您会掉头去寻找一些东西。比如说传统啊,你一直在说的公平与正义啊。我这种读解方式当然也值得反省,那条路当然也可以是那条土路。但在本文中,三个“多年之前”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修辞上的隐喻结构。
韩少功:写作有时是没什么道理的,兴之所至,信马由缰。一个作者在写作之初可能会有提纲,但写作时要放松,要随机,切切不能完全按照提纲去写。
季亚娅:但我们之前谈阅读方式时也说道:一定要回到整个上下文,甚至文本内外来理解一句话。这句话和这篇文本中的另外一些东西构成了一个大的语境。我可以谈谈我的感受吗(韩答:可以啊)?您在《欢乐的工地》中讲到一个观点,在历史叙事中常会有一些被忽略掉或者隐藏掉的“细节”,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尤其是我这种书呆子)常常会读不出那些不曾言说的细节是什么。比如您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提到“又一次逃离的冲动”。我记得很多年前,您离开湖南到海南时,曾撰文说到自己是一次逃离。“又一次逃离”和“多年之前的路”显然构成了一个隐喻群。那么,您能结合“逃离”来谈谈这条“多年之前的路”吗(笑)? “又一次逃离”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韩少功:我这个人哪,有点不安分,总是向往一种比较理想的生活。三十多岁时我从湖南来到海南。那时候我觉得内地的生活有一些沉闷,机关里衙门习气太重。我觉得海南岛像一片美丽的新大陆,“生活在别处”么。那时从长沙到海口要两天,坐车又坐船,颠颠簸簸的,有流落天涯的浪漫。那时官方许诺一个充分自由的经济特区,还许诺开放市场经济和民间独立办媒体。那不就是一个自由天国吗?但在海南从九十年代待到现在,你又会发现,现实同样是很严峻的,市场体制下既有解放也有罪恶。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这些年知识界的变化。原来我以为经过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思潮洗礼,知识精英已经足够成熟。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也就是几个蝇头小利,市场的钱,或官场的钱,或西方的钱,就会搞得很多知识分子没心没肺,摧眉折腰,不说人话,总是用堂皇语言来包装自己的投机取巧。知识分子怎么就这样啊?以前大家坐在一起还经常谈谈哲学和文学,但现在与一些作家、记者、教授吃饭,都是言不及义,插科打诨,谁不谈钱谁就是犯傻,所以很多次吃饭回家你都会觉得索然寡味(插话:所以还不如去劳动呢)。这个时候你肯定会有一些反思,会有一些对自己的不满。反叛也好,挑战也好,逃逸也好,总之你不能不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
季亚娅:您在这篇文章中还这样说,您不相信上帝,因为他 “数十个世纪以来一直推动我们逃离,但从不让我们知道理由和方向所在”。我从中看到的是一种最为深刻的怀疑。您在八十年代就宣称自己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前几天我看到韦君宜写的一篇文章,说到马克思和女儿的对话。有一句:您最喜欢的格言?马克思回答说:怀疑一切。韦君宜说,怀疑是否是革命者的本质?我想问您的是:怀疑在您这儿意味着什么?怀疑是否意味着一种永远批判的姿态?
韩少功:怀疑对我而言,就是寻找生活中的问题,用这些问题去检验我们所热爱、所尊重的知识。我经历过“文革”,在那时尝试过我们的怀疑。那么在一个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体制下,怀疑同样是我们思想创新的动力。世界史少说也有五千年了,再少说也有三千年了。三千年来有制度和思想的各种变化,但据《全球通史》的那位美国作者说,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占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至今还没有一种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上帝存在吗?甚至还可以再问:理想是否可能?这不能不让我们有点沮丧,就像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如果有上帝,他从来只是变换不公,而不是取消不公。但是如果我们放弃怀疑,放弃批判,放弃追求,我们以前的一切所为都成了无事生非。有些伤痕文学描写“文革”中党支部书记强奸女知青,知识分子非常愤怒。但现在老板强奸女员工,搞得公司里三宫六院的,很多知识分子倒觉得没什么,还说嫖娼和二奶都是时代进步的表现。那么你们当年何必愤怒呢?你们最为憎恨的强奸什么时候合法化了?
季亚娅:和您谈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听到您谈到一个词,就是不公不公不公。您是否觉得文学是解决这些不公的一个媒介。
韩少功:文学解决不了什么,但文学可以有限传达一种情绪。但传达这种情绪,与没有传达这种情绪,是有区别的。觉得应该有这种情绪,与认定不应该有这种情绪,也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必夸大文学的功能,但如果没有文学,这个世界可能会更糟糕。
季亚娅:宗教呢?
韩少功:宗教,哲学,都没有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说以宗教和哲学进行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就是历史的应有之义,使我们没有走进天堂但也不至于落入地狱。我有一次说到“次优主义”,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理想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在不理想的生活中间找到一种不那么坏的生活(季:我还没有看到过,这个发在哪里?韩:这是一个谈话,发在《南方周末》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实现最优,但可以争取次优。
季亚娅: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不平等既然是一条铁律,他就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怀疑也不需要了。
韩少功:怀疑和反抗也是一条铁律呵。如果没有这第二条铁律,第一条铁律就可能更烂,更恶,更残酷,这就是怀疑论者的积极和肯定。
(一)(二)(三) (四) (五)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