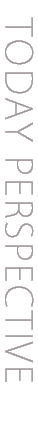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一本书的最深处:读者与作者的对话
韩少功/季亚娅
革命历史的重新讲述
季亚娅:下一篇我挑出来的是《残碑》。我会觉得它是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另外一种讲述。在这本书里牵涉到这个主题的还有一些,有一篇叫做《老地主》的,我觉得它讲过的是革命伦理与乡村人情伦理的对应和区别(韩:对)。《最后的战士》,被历史遗漏的战争的另外一些真相。《当年的镜子》,关于革命记忆的另一种书写。《另有一说》,抗日史中被隐去的细节。
我想问您的是:现在似乎有一种重写革命史的文化现象,如《集结号》《历史的天空》《亮剑》等等。请您谈谈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以及原因。
韩少功:以前的文学作品对历史粉饰得太多,把历史描写得干干净净,容易培养历史幼稚病。就像我在《欢乐的工地》一章中撰写的公路碑文,其实把很多东西“隐”而不说。小孩子看了一些革命电影,觉得革命很好玩,扮家家一样(二人笑)。这是歌颂英雄吗?实际上是贬低了英雄,因为轻而易举就能取得胜利,那算什么英雄?其实历史不是那么干净的,总是带泥带沙,带血带泪的,有很多残酷与痛苦。历史人物经常不是在对与错之间选择,更不是在全对与全错之间选择,而是要面对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一类难题,所以才艰难,才手上有血。
季亚娅:您是说是因为以前的描写太干净了,所以会有这些重写?可是这种重写它会不会也同样是一种简单化的改写与过滤?
韩少功: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在冷战以后,有些人一窝蜂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对革命大加妖魔化,走向了另一种粉饰、曲解、以及简单化。似乎天下本无事,革命是一些烂崽和恶魔出来捣乱。其实在当时革命以前,天下太不太平了,满世界都太无人性了,比如在当时的湖南,民不聊生,生不如死,南军打过来,北军打过去,都是烧杀掳抢奸,人口急剧地减少——这些在地方史料里都有充分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能不革命吗?不抓枪杆子还有什么活路?红色的割据,是其它各种强权割据多年以后才出现的。光是一条军队不扰民,就足以让共产党在各种割据中脱颖而出,最终赢得民心。对革命大加妖魔化的人,为什么不去说说这些情况?当然,革命也会充满着很多悲剧因素。因为社会运动可能失控,可能走弯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手术刀一下去,不但割掉一些坏细胞,同样也可能伤害正常的肌体。
季亚娅:您刚才一直讲到历史的全部复杂因素。讲到那个大历史叙事中的“隐”与不见。可是,面对这种“隐”,我常常怀疑一切又无所适从。那个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呢?换言之,我们有无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韩少功:有两点:一个是深入地了解,一个是全面地了解。所谓深入,就是说尽量取得第一手资料,不要太相信宣传与传媒,就像我去听当事人和亲历者说。所谓全面,就是兼听则明,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季亚娅:您是说当时“左倾”得势肯定是有它很多原因。
韩少功:当年在北大的教员中做过一次投票,评选当代最伟大的人。得票第一多的是列宁,有一百多票;第二多的是威尔逊,美国总统,只有几十票。两者之间差距很大。当时那些投票者都是自由知识分子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党。为什么会有这种投票结果?这是妖魔化所不能解释的。
自然、动物有心、草木有情
季亚娅:下面一组文章是关于自然这个主题的。如《耳醒之地》我觉得是远离城市生活之后所发现的那个无限大与丰富的自然。类似的还有《蛙鸣》《村口疯树》《月夜》《太阳神》《雷击》《CULTURE》《感激》《遍地应答》等等。这些都会涉及到人与自然与宇宙与上帝的关系这个命题。这些文章中都使用一种非常感性的语言来描写您内心最细腻的感觉,因此我想请您用理性的语言进行概括。
韩少功:我们的唐诗宋词里就有很多山水与田园。自然是生命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甚至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如果没有这些动物和植物,没有一种生态网络,人肯定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对自然的取消,就是对人的取消。对自然的漠视,就是对人的漠视。实际上,现代化一直在割断人与自然的联系,至少从感觉上首先切断这种联系。比如我们每天吃菜,但我们不知道这个菜是怎么生长的,似乎它们是从超市里或者冰箱里长大的。有些小孩子就像我曾写在书里的,一看见鸭子就只叫唐老鸭,一看见松树就只叫圣诞树。
季亚娅:说到这里我可以补充一个感觉吗?唐诗宋词里到处说到烟花烟柳,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是烟花烟柳了。后来有一次去北京植物园春游,有一个好大的湖,我放眼一看,果然就是那样,隔着湖岸看对面的桃花啊柳树啊,可不就是像烟一样淡淡浮着。然后我分析它有两个条件,一个要成片,一个要有一定距离,但是现在我们不可能这样去看。所以这么平常的比喻都没法理解其妙处。
韩少功:还有一个简单的词:“人烟”,为什么有人的地方要有烟啊?现在很多小孩子不了解。现在都是烧煤气、液化气,或者用电磁炉,没烟了。有烟就要喊消防队了。这样,很多优秀的文学遗产已经不能进入现代人的感觉。然后,既然我们在生活中已经没有了自然,自杀性的开发也就顺理成章,对天地的友好与敬畏也就难以为继。大家觉得汽车是更重要的,水泥是更重要的,银行与股票是更重要的……一直折腾到空气、饮水、食品都毒化了,这才手忙脚乱。
季亚娅: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您写到“草木有情”,如《蠢树》《再说草木》。之前即使是佛经也不会把草木当成生命来看。但您写到那些植物居然能听懂我们说的话,会因为我们的赞美加倍努力生长,因为我们的批评一气之下不开花结果甚至自杀。哈哈,虽然很违背文学阅读的常识,但我还是想问,这是真的吗?
韩少功:很多东西我们不能用现有知识去处理它。你问的就属于不能处理的多余部分,或者溢出部分。这就是我理解的神秘。当然,现在科学也在发展,比如一些植物学专家会告诉你,我们在砍这棵树的时候,如果给周围其他树做“心电图”,会发现它们出现巨大的生理变化……
季亚娅: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对待它们?
韩少功:是啊,怎么对待它们,会是一个问题。它们虽然是植物,但也可能是有感觉的,与动物的区别可能只在于没有两条腿,没有一张嘴,但实际上可能也有信息传播方式。它们可能很低级,或者低级这个概念并不准确,它们只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传递感受,进行联络,谁知道呢?至少释迦牟尼在当时肯定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把植物排斥在“有情”之外。
季亚娅:我们中国的古代神话是否意识到这点?经常会有老树成精的故事,这就是以人的情感来体验一棵树的情感了。
韩少功:对。文学经常做这样的事,以想象的方式弥补科学的某些不足。文学的功能有很多,孔子说到“诗”的功能时,最后一条是“识鸟兽草木之名”。那么诗也有一种科普功能嘛。文学没有禁区,向一切事物敞开,把能解释的和不能解释的,能理解和不能理解的和盘托出,因此它不会回避神秘。这本书里有一章《瞬间白日》,描写黑夜突然明亮如昼。这件事我至今没法理解,请教了很多专家,也没法得到合理解释。但是我是当事人啊,毫无义务要建立一个禁区,把不能理解的事情给排斥掉,所以把它记录下来。
季亚娅:下面我挑出一组写动物的,这些都写得非常动人。您早年有一篇作品叫《飞过蓝天》,那里面的鸽子晶晶还是理想化的拟人描写。但现在不同,在《飞飞》《诗猫》《其中的异犬》《三毛的来去》中,动物的情与理,动物与我们之间类似亲情的关系都有非常动人的呈现。还有一类作品是《养鸡》《小红点的故事》,您观察到人身上某种和动物共通的天性,比如:鸡也有排外天性,他鸡即地狱,这和人类的排斥陌生人的天性多么相似。
韩少功:人和动物虽然有明显的分界,其实它的共同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说有些成语,“垂头丧气”什么的,我以为是描写人的专用词,后来发现鸡呀狗呀都是这样,它们情绪不高的时候都是垂头丧气。人身上的动物性比我们想象的多。还有“趾高气扬”的情况也是。
两篇特殊的文章
季亚娅:有一篇文章我是真的没理解,《很多人》,您好像就是把一篇族谱抄录了一遍。这是怎么回事?
韩少功:当时我看到那个族谱真是很震动,一点也不觉得它枯燥,一点也不觉得它平淡。你想想,这么多名字,都代表着人,代表着一生中很多故事,但一切都在历史上被淹没了,只是留下一个名字。甚至有的人的名字还失考,尤其是那些女的,只是张氏李氏什么的。
季亚娅:对啊。我正准备说这个,女性在族谱里永远就是某某氏,永远处于无名的状态。
韩少功:也许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罗列下来,向类似我这样的人传达这种震撼和感慨(插话:这个简直就是禅嘛)。你可以想象,我们以后就是这上面的一个名字(插话:您还是不会的,我说不定连这样的名字都没有了。二人大笑)。历史有多长啊,任何名人都只是名震于一时,任何大数相对于无限来说都只是零。
季亚娅:还有一篇我认为其实是动物主题中最好的,我把它放在这里说,《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这篇其实您只写了标题,其下通篇留白。如果说《很多人》是有意味的沉默,这一篇就是有意味的空白。这些空白它是什么?
韩少功:有时候文字苍白无力。我们再自信,也都会觉得自己笨,觉得文字表达不了某种东西。
季亚娅:那是否和禅很像?那些不曾言说的东西可能比言语本身更重要。
韩少功:说出来就不是禅。
季亚娅:这个让我想起之前的雪灾,面对风雪我会觉得一切的解说都比不上朴素地用镜头展示灾难的场景本身来得动人。可是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有了影像以后是否我们就不再需要文字了呢?影像时代文学何去何从?
韩少功:影像也有缺陷,比如人的某些奇妙想象,你就无法用影像表达出来。钱钟书说过:爱神之箭射中我心——这个意思如何用影像来表现?你画一支箭射穿爱人的心脏吗?说爱像“电击”一样——这个意思你如何表现?展示一个变压器再加上电线和插座吗?那是不是太恐怖了?其实,任何一个优秀的比喻,都是影像难以表现的。
季亚娅:这样一说我想起一个比喻: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我会想:流风之回雪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美法呢?可是每当我看到电视剧里的洛神都会沮丧,可能正是这个道理。
在文本中演练“心身之学”
季亚娅:首先可以看看我称之为反对教条主义的一组文章。这其实是文本中无处不在的您的知识观,它听起来很枯燥,但是与文本结合起来却是妙趣横生。《哲学》,农民很害怕书生下来和他们讲理论。农民的理论就是:干部多吃多占就好像牛偷吃了禾,鸡偷吃了谷,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也不是什么大事。《蛮师傅》说,蛮干也比空谈好。因为实际生活中蛮干往往有很多无奈,比如少钱。您说,“就是一个同胞,如果不熟悉乡村这些年的变化,要会心于老篾匠的比喻和概括也决非易事。正像我们不曾亲历西方历史过程,要读懂他们的各种理论,大多只能一知半解”。这还是强调亲历对于历史以及知识与理论的重要。关于这一点还是要请您作一个总结,因为它一直就在您的思想脉络里。
韩少功:任何知识,都是对现实对象的一种简化表述,只是有时简化得多,有时简化得少。如果要是说完整地表达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那几乎不可能。我们谈论一个杯子,从最开始的颜色、质地、款式到它的分子结构原子结构亚原子结构,可以无限谈论下去,写一本厚厚的书也谈不完。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能简化,只能对于任何知识都要抱一种审慎态度。我们知道它是有用的,但是它又是片面的,几乎是瞎子摸象的产物。
写《雷击》这一章以前,我认为信神信鬼是迷信,说给母亲做了一件棉袄就会被雷公放过,这怎么可能呢?但到了乡村以后,我才注意到某些迷信的合理性。那个地方几乎无处躲雷,人们也没钱来安装避雷设施。你怎么办?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孝子不遭雷打,是人们面对雷电时的自我安慰。人们没钱买科学,但自我安慰的权利还是有的吧?给自己壮壮胆还是必要吧?这其实也是心理医生常做的事情。
季亚娅:是啊,这正是我的下一个问题。您从“亲历”和“体认”中理解了这些称之为传统伦理的东西……
韩少功:很多看似乱力怪神的东西,是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根据的。西藏人为什么宗教感那么强?在那样环境严酷的雪域高原,经常是几百公里内都找不到人,更不用说找到医生了。那么人生了病怎么办?牛羊生了病怎么办?所以他们只能求神。即便神不能治病,但他们因此获得了精神调理,有什么不好呢?批评者既然不能随时给他们空投医生和药品,那么一味的指手画脚之下,是迷信还是“科学”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一) (二)(三)(四) (五)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