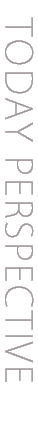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程永新:中国作家当中被高估和被低估的倾向都很严重
木 叶
“我对程永新后来放弃写作觉得十分可惜。”余华曾有此言。而今程永新将十余年前便初步完成的“流浪三部曲”陆续修改推出。第一部便是这《穿旗袍的姨妈》。
程永新,笔名里程,《收获》副主编,马原说他是“少数真正懂小说的人”。《顽主》一名是他编发时拎出来的,《活着》《高老庄》《妻妾成群》《务虚笔记》的首次发表均与他有关,这些名字的背后是另一些名字,另一些意蕴。
采访时,《收获》恰满五十周岁,他忙于特刊。他见证了这一文学期刊正好一半的年华:二十五载。
程永新是喜欢自己小说家身份的,贾平凹“震惊”于其《穿旗袍的姨妈》。至于他作为编辑的声名是否遮掩了其小说的才情,你需要自己看取。
“我给我自己的这个小说打60分……现在80%的小说都不到60分”
木叶:你在散文《祝你生日快乐》里提到自己的姨妈“穿戴整洁”,有着“款款的身影”,长篇里“穿旗袍的姨妈”和生活中的姨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重合?男主人公“骆驼”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程永新:姨妈生活中的原型有一些,但不完全是。骆驼也不是我,但肯定是我同时代的人,我对这样的人非常了解。
这个小说是“流浪三部曲”的第一部。我采取一种比较老实的写作方法,可能有些批评家觉得你也鼓吹、推动过先锋写作,但你在写作的时候并不极端……其实我也有一些探索,比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交错的叙述视角,有些批评家觉得你是不是后来修改时增加了这些变化?其实不是,我1995年写完的草稿就是跳跃的视角。普鲁斯特主要是回望过去,我增加了未来的东西,增加了主人公“此时此刻”对未来展望的叙述视角。
木叶:贾平凹在序言里说,“姨妈,穿着旗袍的姨妈,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在那个荒唐年代的形象吗?” 你真的有意用“姨妈”来象征“妈妈”?
程永新:这是他的一种看法。我在写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把姨妈比作国家、祖国,我想到的是她这种生存方式代表了中国的好多人,现在也是这样,搬个家你让老年人扔掉点东西,她什么也不扔。我们的上辈人都是这样的,克勤克俭,非常清苦,弄到最后不知为了谁。死后大家为了她的东西争。
木叶:里面讲到了一个同性恋的情节,兔子和“我”在一个被窝里相互抚摩,这还使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些故事。设置这个情节时,你一定有什么想法吧?
程永新:我是觉得在那个时候,生活当中的很多原生态的元素都存在,可能就是人性吧,在特殊情况下,人相互之间需要安慰。我写到他们去拉练,有死人在屋子边上,很恐怖,两个孩子之间很自然地可能产生这种行为。我想说,即便在当时这种年代这种行为始终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后来才把它叫做同性恋,性猥亵。
木叶:涉及文革的小说有王朔的《动物凶猛》,按姜文的翻译就是阳光灿烂,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则是另一个味道,你这一部延宕十多年才拿出来,同样写这段历史,特异之处在哪里?
程永新:我还是比较注重人物的内心。我在修改的时候,已拿掉许多人物的内心独白、心理分析,这是为了现代的读者。我觉得小说的节奏要加快。我希望后面的小说也能这样。多年前的初稿格非、余华看过,格非当时就讲,未来小说的节奏要有变化。
木叶:那是否会让人觉得是在迎合读者?
程永新:我小说的故事性不是很强,又因为是成长小说,所以阅读的心理节奏很重要,如果我再作细腻甚至拖沓的心理分析,不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不是迎合,是一种需要。而且这个主人公也来到了九十年代,他本身的生活节奏已经加快了。
木叶:也就是说小说人物要求作者加快节奏。在这本书后记里你提到《大卫?科波菲尔》是真正的经典,我想知道在你的阅读版图里经典还有哪些?
程永新:我不像某些人只喜欢某一类,我是各种类型都有一些喜欢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肯定是,福克纳的《喧哗与躁动》也是,福克纳的中短篇也都很好,米兰?昆德拉的我也很喜欢……
木叶:就是说先锋的和传统的不管,只要写到极致的都算……
程永新:其实,“先锋”这个概念八十年代的时候更可以理解为文学的各种创新和实践……八十年代我们把王朔也放到余华、格非那些人中间,有人说王朔跟他们风格不一样。我觉得当时出现王朔的小说是不太容易的,用新北京语言来写作的,他跟之前的那些北京语言写作的小说也不一样,他对有些陈旧观念和陈旧语言的消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是新的探索。
一段时间的文学,一段时间的精神产品你用先锋这个词,是一种需要。其实,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你说阿城的小说是先锋小说吗?(是。)那么王安忆呢,王朔呢?但很多人觉得不是,当时我编过一本书,用的是新潮,我没用先锋这个词。我当时就找不到一个词来概括当时的文学状况。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处于大爆发状态,那么多流派都进行了实验,用先锋或新潮,都无法概括。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做的事情要大于这个概念。
木叶:你有意识写先锋小说吗?
程永新:啊,没有。小说的形式应该根据内容来定。
木叶:你的小说1995年左右(大体)写好,延宕多年出版,你自己解释说是懒散、浮躁,我觉得应该有出于小说文本本身的考虑,当时小说到底还缺什么?
程永新:我当时想写一个人的流浪史,也完成了,但是一个大的东西没想明白,这个小孩不断成长,后来他的境遇变化了,经济状况变化了,他还是不知所措,还是觉得自己在流浪,为什么是这样?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原因,社会在他身上、灵魂里打上了太深的烙印,就是他没有办法真正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来完成人格的转变。
木叶: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你在十几年后的今天要拿出它来?
程永新:拖这么久,还是生活的欲望太强、想法太多。我时不时地想到我的这个作品,觉得再不拿出来就跟这个时代相隔太远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对现在的小说创作不满。我给我自己的这个小说打60分,不是谦虚,我后面还有一句:现在80%的小说都不到60分,没过线,不及格。
木叶:还听你说王安忆孤独,我来陪陪她。
程永新:在文学圈,感觉上海作家能拿得出手的说来说去就是王安忆,她确实不错,很好,但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不能只有她,这太可悲了。我也曾讲到孙甘露、须兰,包括巴金的儿子李晓,都是非常好的小说家,就是因为上海人的浮躁,因为生活的欲望太多,想做这个,想做那个,后来这些人都没写下去。我想流浪三部曲后面两部出来之后,批评界会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说法,我对它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我退的稿子,后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好作品的,没有!”
木叶:你又是编辑又是作家,见你曾自称“业余”作家,你更满意或是更看重哪个身份?
程永新:更看重作家这个身份,尽管我不是很有职业心态。八十年代时马原说作家要有职业心态。职业心态就是像王安忆、迟子建、苏童等优秀的作家那样,不停地写,哪怕在写作的低谷依然有那么一种毅力。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你要经受好多批评,特别像苏童,非常不容易,曾那么大红大紫过,然后到了一定时候,别人对他的批评,认为他是(通俗作家)……他很不容易。经历过大起大落之后,慢慢他的状态又开始回升。
木叶:当朋友们都拿出有分量的作品,你就没有焦虑吗?我指的是一个作家的那种野心。
程永新:那倒没有,这些作家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的每一点变化我都很关注,为他们高兴。像格非,《收获》五十周年的特刊,约他写中篇,非常棒,我说我喜欢你的这个中篇超过你的《山河入梦》。
人的经历、气质和想法的差别比较大。余华的经验、孙甘露的东西,我没办法跟他们比,反过来说,我的这些体验他们也不一定有。我写的是极其敏感的人物。有个细节,别人的腿被撞疼了,主人公感到自己的腿也在疼。在第二第三部里我会加强这一点,它的独特性会越来越显示出来。
木叶:你流露过这样的意思,作家是一个无名小卒时,你一个编辑可以是他的老师;作家名扬天下后,你就是一个改错别字的了,甚至因自己当初的坦率直言而与他反目为仇。作为一个编辑,你心中有没有一个高标之类的人物呢?
程永新:我对自己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我知道一个好编辑应该做哪些事情,从八十年代就知道。孙甘露在文章里讲过编辑是“为作家提上衣的人”,让他们施展才华。我想象当中的编辑,有敏锐的感觉,有理论的素养,有艺术的知觉,能预感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正发生什么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推动文学往前走,有点像足球场上的“中场发动机”。
木叶:八十年代《收获》的几次专刊都很有影响,但那时文学真是一回事儿,现在同样组织这么一些专刊,影响怕是不会那么大了。
程永新:会和八十年代结果不一样,但你努力了之后还是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效果。
木叶:《在路上》是一种精神,《洛丽塔》简单的人名就意蕴无尽。据我所知,《五花肉》在《收获》发表前,王朔在给你的信里列了五个标题,你拎出了《顽主》!毕飞宇的《平原》发过来时文件名就是“长篇小说”,你在帮着命名作品时特别看重哪一点?
程永新:为小说命名是很困难的。题目跟内容互为映照,好的题目提升小说,差的题目给小说做减法,让小说落下去。大作家和小作家在题目上就有表现。改过的标题非常多,我一时想不起来。上回尤凤伟有个长篇,主人公一个叫双桃,一个叫双樱,小说写得还不错,但题目很俗。跟他来来回回,后来那个题目(《色》)也不是很满意。最近拿到一个杨少衡的小说,一个中篇,很好,标题也不满意。
给人家改坏了的标题很少,我们主要是给作家一个参考的意见。
木叶:具体到内容,名家的作品也会让他/她改吗?
程永新:也改。像格非的《迷舟》,最初拿来时像马尔克斯小说的翻版,叙述语气太像了。我就跟他说,模仿的痕迹还是要拿掉一些,另外,这个故事是不是还可以写得更完善有力些。格非的了不起就在这个地方,他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改完,看了之后我很惊讶,跟以前的小说完全是两码事!
这一次他为我们的第五期写的中篇叫《蒙娜丽莎的微笑》。他写完了又说我不发了吧,因为觉得不好。我们主编李小林说你发给我们编辑看一下,发过来时,我去欧洲了,我们另一个编辑看了,李小林也看了。觉得有意思,写了一个大学生自杀的故事,但有地方不满意,提了修改意见。我回来看到的是他修改过的稿子,很激动,非常棒。好作家总能找出感觉。
当然越改越差的人也有,太多了,很多人是不会改小说的……
木叶:有没有人被《收获》退了稿,觉得你们眼光不行,有偏见,或是就因被退稿而觉得丢面子的。
程永新:丢面子不大有。我们跟作家像朋友一样。作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出来后得到更多人认可。我们尊重作家的意见,一般都可以沟通。真有不愿改的,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就算了。
木叶:有没有首投《收获》被退稿,在其它杂志发表出来后反响很大,最终被认为是好作品的。
程永新:我们不用的小说被其他刊物用了,这个太多了。但是你说用完了反响很好的,几乎没有。我跟走走就讲,这么多年来,我们能够比较自豪比较骄傲的是,我退的稿子,后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好作品的,没有!我们也比较慎重。
那时候李杭育有个中篇,我们退后由《人民文学》发了,王蒙还写了文章推荐,那么这个来头很大了。李杭育就来跟茹志鹃说,你们《收获》看不懂我的小说。我就说你这点东西有什么看不懂的。他写一个老头在爬山,爬得很艰难,中间又休息,象征我们的国家,我是觉得用三万多字写这个东西太枯燥,用一万字就够了。 他当然不会听了。这时候他刚刚得了一个全国小说奖,《最后一个渔佬儿》,那时一个奖蛮牛的。《人民文学》当时也是很不错的刊物,后来还是很多人看了觉得这个小说太差了,马原跟我说你根本不用担心你退了一个好小说……后来作协来调查,我说我退的,当时我还年轻。
木叶:我注意到,在《到处都在下雪》一书的封面折页上对你的介绍文字中,写有“中国当代最有名的文学编辑”一语,可能是出版社所加,但我想问问你怎样看待“最有名”这一修饰语?
程永新:最有名不敢当。在八十年代,我很尊敬的大编辑有李陀、朱伟、范小天,当然还有《收获》的李小林,我在编辑业务上如果说有什么成就和她是分不开的,她是我的老师,虽然没有拜过师。当下的优秀编辑有宗仁发、林建法、李敬泽等。文学辉煌的宝塔是这些优秀编辑扛起来的。
“整个批评界非常浮躁,认认真真读作品的人很少”
(一)(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