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詩(書)話》3:艱難重生的玫瑰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9-19 08:56:12
/ 个人分类:评论
查看( 237 ) /
评论( 3 )
艱難重生的玫瑰——讀北島的詩《時間的玫瑰》今天7L9_�v9b�[�J�S今天�z�~�z$g�z�I
`7p江濤�\�z#Z�b8U0今天�a s2Y�_:k&]�J&M
人們讀北島,如今,很多時候,已不是讀他的詩,而是讀他的人——他的被多重政治化的人生色彩,已然強烈地蓋罩了他過去和今天的詩歌寫作。
�i�@
^�w$m/i
o�y0今天�{:\*g!q1T3H
的確,過去那些熱血青年正義的振臂呼喊的詩篇,正逐漸被當代詩歌藝術所否定。在那個人們極度渴望釋放被壓抑情感的政治動盪年代,那些在荒山野嶺度過青春(上山下鄉)的年輕人,那些被政治偶像愚民了幾十年的無知民眾,他們只需要一把簡單的、觀念的控訴的聲音——那是他們被禁錮多年的認知能力僅且能夠接受的。很難想像,那時的普羅大眾如何能理解當代名稱如萬花筒似的各門各派的中國詩歌。因此,那時北島詩歌代表的是與極權對抗的平民階層的話語權的爭取——懷疑和否定——在這些話語裏,充斥著的是被二十七年革命文學洗涮過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語調和言辭——可這偏又是必然和無法拒絕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既然對文學藝術的謬誤和扭曲已深入到當時中國文學的肌理,那麼它的反抗和偏轉力量,必然只能從其內部產生——那是一種政治對抗的語言表達,卻正是一種呼喚人權與良知的呐喊。因此,北島初期的詩作大多是政治抒情詩,它表達了被壓抑幾十年的民眾心靈的求生欲望——那麼有力,卻那麼單純,那麼明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以及“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此簡單的歸類,一如當時一刀切劃分的階級成分和政治面目,甚至連矛盾修辭或反諷之類的語言陌生化手段都不用——但,讀者,尤其是今天的讀者們,請你們不要蔑視和譏諷,他們,就是中國現代詩歌在五四後的另一次突圍:語言和修辭已是次要的,用大眾能一聽就懂,能迅速引發共鳴並能和著粗重的呼吸,揮臂朗誦的時代流行話語表達出懷疑和否定,才是這次靈魂突圍能取得勝利的關鍵——是他們,在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歷程中接住了五四文學先鋒們傳遞的精神薪火的第二棒——這難道不值得人們紀念和尊敬嗎?
�a�y�\+]�c�R:M:U�r�h0
;r6Z"}$I
\1^%c0由以上論述所引出的,是解讀北島近作《時間的玫瑰》的內在起點和核心。當北島寫作這首詩的時候,已是他流亡國外十多年後。此時,中國的政治格局依舊,但經濟面貌卻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門重開,西方的現代、後現代的各種文化思想著作的迅速譯介和傳播,如巨浪衝擊著中國新一代知識份子的心靈。日漸穩定和寬鬆的學習研究環境,使他們有機會從容不迫地不斷調整和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他們逐漸能夠立足於各自不同的研究領域,對時代表達自己的見解和意見。而根基於“語言”的哲學和文學研究的批評理論,正在把詩歌藝術的巨大變革,悄然帶進了國人在紙媒和互聯網上轟然蓬勃的中國當代詩歌——此時,寫詩似乎已不再有被流放或監禁的巨大風險,隨著汪國真詩歌的流行、熱賣,及後來所謂“知識份子”與“民間”、“上”“下”半身二元對抗的喧嚷;一年十二個月有十三次詩會(或二十六?);動輒獎金過萬元的無數以人名地名命名的詩歌獎項;各種官方或民間詩歌刊物雨後春筍般湧現,如狂歡節上亂扔的雞蛋……寫詩,開始變成一件能出風頭、賺名利的事情——這是否就是那句“一個招牌掉下來會砸死九個詩人”的黑色幽默至今仍合理流傳著的原因?而此時,老北島和他的詩,也正被當代“詩歌新貴”合理地遺忘和唾棄——而對詩歌語言藝術的深入研究和理解恰是他們的批判武器。此時的老北島,如人們所見、所傳,面對著仿佛來自語言內部代表們的批評和責難,顯得惶惑和力不從心——在此,筆者只是直陳這種現象而無意修正——還是轉入正題,從文本解讀入手,分析詩中透露的訊息吧:今天 H5R ~�W-F�k0r�r
今天�`�w:T.p+x�F�U
1.題目:玫瑰的名字今天 }�v�v�p5[�G�F�\
詩的名字——《時間的玫瑰》。生長在世間的玫瑰,盛開,然後凋零。盛開時的燦爛、嬌豔、芬芳轉瞬間歸於塵土;而生長在時間的玫瑰,是玫瑰盛開與凋零的永恆的輪回——如數不清的花瓣的開合,幻影般的幽靈的呼吸,起伏、錯落、綿延,生生不息——仿佛我們生命中那某個不可言喻的顫慄時刻,周而復始,如里爾克的詩句:在中心有一個偉大的意志暈眩。今天-t�` ^�U$P�Y#R%v
在這首詩中,“時間的玫瑰”不僅是題目,她還重複出現在每一節的最後一句——仿佛成了詩人生命歷程中如影隨形的心魔——“一個偉大意志的暈眩”——展現出里爾克《玫瑰集》中用詩句編織的“一朵玫瑰,就是所有玫瑰與自身……如果沒有她永不知如何說,我們的希望也無從依託,在持續的出發程途,途中又有溫柔的間斷”。(何家煒譯)今天�n�B�@#`(x6z�c.|-D
�F�B0C�V/^5W&H:t02.第一節:離開故土的玫瑰今天�z1N�`�` H�V
當守門人沉睡/你和風暴一起轉身/擁抱中老去的是/時間的玫瑰
�X�C�H*h�e+K�G�A6L.Y0——敍事一:在那個難以磨滅記憶的年代,古老東方之國的大門緊閉,承擔守護職責的“守門人”仿佛也進入了長眠不醒的黑夜之夢——他需要一場風暴,然而風暴也不能把他喚醒——大門依舊封閉,暴風撞上古城的銅牆鐵壁,粉身碎骨,折翼而返。“你”——詩人,隨強力語言的風暴來臨後折返,離去——然而那“心魔”,卻被緊緊擁抱于詩人的懷中,不曾離開,憔悴地開放——“玫瑰”離開故土的必然命運。
�S'G�V'o5O A�S8B6n0今天2C�f*m�Z�G�z
3.第二節:流亡途中的玫瑰
8F6|�X6J(x�E0當鳥路界定天空/你回望那落日/消失中呈現的是/時間的玫瑰
'J�x�I�|�c$p�H�K0——敍事二:像一隻沒有歸途的候鳥,天空是他所有的路。故國的落日似無所關聯,然人生的落日總情牽鄉愁——失去才知珍貴,某物的出現常常在某物消失後才強烈顯形——仍舊是那“時間的玫瑰”、那“心魔”、那“意志的暈眩”。今天%\�H0@ F5l8V�?
6[�z,u�N*R�H!x
u�H04.第三節:受傷的玫瑰今天(X�x5{6E�M�J9? Q
當刀在水中折彎/你踏笛聲過橋/密謀中哭喊的是/時間的玫瑰
#b�z2L(B3u�\1C�a0——敍事三:此段用了兩個典:李白在《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中的不得志的鬱結憂憤:“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毛澤東在《賀新郎別友》中的癡情、悲情、絕情:“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恁割斷愁思恨縷。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墮,雲橫翥。”在這裏,“時間的玫瑰”第一次以人物的形象出現——一個哭喊的女子——人們可以密謀奪取社稷江山,卻不可以密謀獲取“詩意”——她的不可褻瀆在於能承載江海的性情,卻不容於國家機器精密零部件的毫髮計算。
�e�u%i4Y�A0
.j"y%F7s�i�r�d-_�e05.第四節:玫瑰的預言
�U;G�F�o�B;A G%e�e0當筆劃出地平線/你被東方之鑼驚醒/回聲中開放的是/時間的玫瑰今天�z7Y�{"Q�G�H�`&x�P:H-h
——敍事四:積攢起無數新的一天,就是一本厚重的新時代書寫之頁。黑夜暴風摧不醒的人們,從自身的沉睡中覺醒。醒鑼是中國特有的召集與告示之物,讓人精神為之一震,茅塞頓開——“時間的玫瑰”是醒鑼的回聲,在回聲中開放,書寫新的時代與際遇。今天'G,|4O�z"m'R/G4O&f
�v2Y�^8L�v
x06.第五節:玫瑰的重生之路今天
s�j�t�?�C0r,{4\
鏡中永遠是此刻/此刻通向重生之門/那門開向大海/時間的玫瑰今天1H3g�a9`�g�z�z#X3_
——抒情與讚頌:此段的用典是一幅畫:山德羅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生》(約1485年)。臘神話中,泰坦神祗克洛諾斯閹割自己的父親烏拉諾斯後,把他的陽具投入大海。陽具在海中漂浮,變成許多白色的泡沫,這些泡沫便孕育出了美神維納斯。她出生即成人,思緒沉靜,眼睛透露出對未知世界的略帶困惑的思考——一個憂鬱、哀婉、美麗女性形象,在她身上寄寓了畫家的人文主義理想,一種浪漫情懷,渲染了生命主題的詩性。而令人欣慰的是,北島的“時間的玫瑰”是在敲響東方之鑼的中國——“東方的繆斯”,她正踏過重重的波浪,走在步履艱難的重生的路上……
)V�W([�~5W%J9H/D�d2z�V�n�}0
�N�y'j8O.[6J�e�k5U07.形式與物象
�]&g6O(X+l0《時間的玫瑰》共五段,每段的前三句,作者先以意象語言鋪敍其言之有物的“情景”或“情思”,而後皆以 “時間的玫瑰”句殿后並重複點題。現代敍事學將“重複”敍事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敍述者對同一事物、事件的反復敍述;二是相同、相似命題或敍事結構的排列。“重複”敍事是一種強勢的結構格局。在此詩中,“時間的玫瑰”的反復吟詠,既是同一事物的反復敍述,也是相似敍事結構和敍事語調的回環式遞升——如玫瑰從含苞到盛放;如詩人內心的激情,從痛惜中的隱抑到情切的呼喚。“重複”敍事,能營造出餘音經久不息的閱讀感受,從而強化了敍事的審美效果;而詩歌敍事內容的豐滿與“玫瑰”自然物象的生長的平行對應,又使《時間的玫瑰》具有了意象與物象同步同構的藝術形式。
8u�I�^�e�A�A�p0今天�R"O�D-X&o6W�~
“時間的玫瑰”是北島的“暈眩”,被他在多次訪談提及,甚至成為了他的後來一本書的名字。她寓意的是詩人的“詩歌女神”,她的形象更在北島最近的一首詩《過冬》中得到了確認:今天�E"r�J�\�k
誰是全景證人/引領號角的河流/果園的暴動
�p�n�x$b _�O9t�K�w�T0聽見了嗎?我的愛人/讓我們手挽手老去/和詞語一起冬眠/重織的時光留下死結/或未完成的詩
�o0e�Q,v,O#N%c4K0今天 |+U!L7]�{�Z
《時間的玫瑰》標示著詩人北島從對國家政治的否定懷疑的詩歌寫作出發,現在已走在了對語言本體的呼喚與回歸的路上——寶刀未老,理想主義的浪漫情懷依舊——然而,詩人北島最終會否發現,語言即是政治,“詩歌女神(美神)”就是政治本身——她並不哀怨,她擁有著強大的自我創造、自我更新的能量——從她變形於浸泡海水中的被閹割陽具的無中生有的出生,即可知其本性之二一。今天)G�y+s�p�]4^�^�b�[.k�e
2008年4月今天 C8h0K�w�R
附詩北島的詩《時間的玫瑰》
�}�P�t t�X�r)q-r0當守門人沉睡 今天�^�Y�x%K(] k(\1C4U0N
你和風暴一起轉身 今天�g4{+o"o(H9a�X�@5n�w
擁抱中老去的是
�c2~$^)~1D.I0時間的玫瑰
5X�l�G�A
Y�V�B0今天"z/R3U ~1\$J�Q
當鳥路界定天空 今天�y�?�?�m Z�|�F�B�K�Z
你回望那落日 今天�x8t4a�};n
消失中呈現的是 今天�k�U�x�~�k�U�l
e�d�f8w X
時間的玫瑰
'x�^,b�w�n�R:K.G�j;?0今天 i�T/O9y
g�k
當刀在水中折彎
W
q0n6h4{;\0你踏笛聲過橋 今天�\ a2_�?.v�d�w�c
密謀中哭喊的是 今天+g�j*a%g�X3v
P�v
時間的玫瑰
%W
L)y�k(g0
-@/^�[1K6^�g�x�r�J0當筆劃出地平線 今天�T-n�t2R#_�`'O
你被東方之鑼驚醒 今天�Y�s)o!y;f�m)i
回聲中開放的是 今天 P�P)M/q�@
r�@*A0e
時間的玫瑰
i5B�c3v�S�W�x0H.z0今天!n6}�N7R�Q�r�E�m�~
鏡中永遠是此刻
�a�V4U#M!h�V,d�D9l*E0此刻通向重生之門 今天(_0}"p'W�r�d
那門開向大海 今天0H @�G�L�g
時間的玫瑰�E�J�@'q([!u�e0今天�|:` m�@
p�o�S�L�R/h9K[
本帖最后由 江涛 于 2010-9-18 22:47 编辑 ]
论坛模式
推荐
收藏
分享给好友
管理
TA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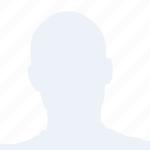 域外菊发布于2010-09-20 17:20:46
域外菊发布于2010-09-20 17:20:46
-
人們讀北島,如今,很多時候,已不是讀他的詩,而是讀他的人——他的被多重政治化的人生色彩,已然強烈地蓋罩了他過去和今天的詩歌寫作。今天)e�V4s�r�D�p�R�l+w
当代诗人中,像北岛一样坚持下来的不多,以坚持诗歌创作的同时能坚持自己的人生信仰的更少,这也人们更关注北岛的一个原因。
-
 紫鵑
发布于2010-09-23 11:45:14
紫鵑
发布于2010-09-23 11:45:14
-
文學≠政治
�Z�~�M�l#A5B%C�^如果政治意圖向文學靠攏
�w#Y�~�P�u)J�g我還是會奮力將它拉回文學層面來閱讀
,S�g�T�G�_�]
v,x(D回到最原始、最自然的狀態 Y�`�q�g�X3?�}
還給它一個純淨的空間今天�k3S�M%W�T�y�@
2{�x�C�x&u�y
時間的玫瑰今天,k9x8]*Y�M�A9f9H
是當年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
-
 江涛
发布于2010-09-23 20:22:49
江涛
发布于2010-09-23 20:22:49
-
是啊,读北岛的诗,怎可能不跟“政治”扯上关系?www.jintian.net.m$V�i�K�f
�x�W7k�|1G/S�O�}�E/d但“政治”有两个指向,说什么,是政治,怎么说,也是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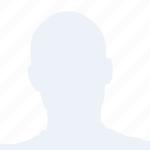 域外菊发布于2010-09-20 17:20:46
域外菊发布于2010-09-20 17:20:46
 紫鵑
发布于2010-09-23 11:45:14
紫鵑
发布于2010-09-23 11:45:14
 江涛
发布于2010-09-23 20:22:49
江涛
发布于2010-09-23 20:2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