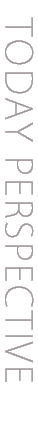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对话: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与长篇小说创作
李敬泽:我比较健忘,十岁前的事差不多忘光了,所以当不成小说家。但是,我对过度强调成长记忆的影响非常怀疑,这就相当于说,我是我爸我妈生的,所以我这样,这当然很正确,但这种自我的循环解释有什么意义吗?汪政说这里有一个“情结”,我很赞同,什么叫“情结”?就是毛病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现在都四十上下了,还整天唠叨你的成长记忆是不是很变态?是不是你除了所谓成长记忆之外就没什么别的记忆可用?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六十年代作家已经习惯于一种文学青年式的自我想象,到现在拧不过来,成长记忆青春期什么的,现在由“80后”小孩来念叨还差不多,你得想想,你是个中年人了,满脸风霜,事业小成或不成,还扯这些东西有多大意思吗?你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志向就是没完没了地研究考虑你是怎么长大的?
“成长”当然是个普遍和持久的文学主题,但你的成长记忆不过是你的出发点,由此出发你去冒险,走很长的路,见识世界之大。而且,成长记忆最终总要长成吧?不能老长不大吧?如果莫言、王安忆现在还老念叨他的成长记忆就会很滑稽,我们这一代现在应该学会像个成人一样看世界、看自己。
写不写“文革”,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你一写长一点的东西,你就找到你的“成长”、找到“文革”,这说明什么?这两样东西是你自然领受下来的,是摆在那里的大叙事,除此之外,你找不到足以支撑一部长篇的大叙事,除了你成长的过程你想不出命运的其他方式,除了文革给定的历史节律你看不出别的节律,这难道不是问题?
三、个人化的迷恋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
朱小如:当然,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呈现的面貌,可能比前辈作家们更趋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如林白、陈染等人的“女性私人化”写作。余华虽然在《兄弟》后记里谈到关于如何从个人的独特的“窄门”出发,然后走向“宽广”的想法。但《兄弟》的实践似乎并不成功。我最近又补读了韩东的《我和你》与陈希我的《抓痒》感觉不好,似乎是走向了“男性私人化”的“窄门”永远也出不来了。而相反林白的长篇《妇女闲聊录》到是走出了“女性私人化”。艾伟的《爱人同志》曾经试图从“人物深度”上寻求长篇小说的突破给了我很深印象。听说艾伟的《爱人有罪》长篇系列似乎走得更远一些,脱离了“成长”记忆的范畴。治纲说已经读过,可能更有体会。
汪政:韩东的《我和你》与陈希我的《抓痒》这两部作品我也读了,由于失去了文学史的意识,现在对一部作品进行价值判断变得非常困难,同时又非常容易与轻率。这两部作品特别是韩东的《我和你》是非常有想法的,但是太明确了,太专一了,于是也就显得单了。现在这种叙述已经渐成套路,表面上好像已经从成长叙述中挣脱出来,但视角依然狭小。相比较而言,我认为刘庆的《长势喜人》就处理得比较好,它是个人的,但更是超越的。在反对宏大叙事之后,是不是就得一味地走私人或个人化叙事的这一条道?它们是不是全然对立的?这些问题刘庆以自己的创作作出了有价值的回答。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确实各有各的文化功能,如果将长篇当作短篇,那么个人,那么尖细,杯水波澜,点滴情绪,显然会造成整个文学功能的萎缩。
李敬泽:《我和你》没看,但《抓痒》看了。陈希我可能受了日本小说的影响,也有些英国“密室”文学的味道。就《抓痒》而言,视角狭小是它的力量所在,灯光打在密室里、两个人身上,有一种孤绝的广大和庄严。
私人化现在差不多变成了一个不名誉的词,我觉得这里边有误区,很容易形成新的自我宰制。是否就存在一种明确的界分,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超越的?什么是私人的,什么是公共的?历史、政治这些东西怎么可能被阻挡在私人生活之外?存在如果不是在个人层面上被领悟,它怎么可能超越?假设这里有明确的界分,那么文学所应当做的难道不是把它打通?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承受90年代争论的混乱,当时那么提出问题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可以放下了。文学可以不必在人类经验和人类生活中强分出什么是有意义的或者意义更高更大的,什么是没意义的或者意义较低较小的——这种思维演变到现在已经很变态了,已经变成了只有底层、民工是值得写的,写别的都是道德上可疑的。
有朋友提出,过去是怎么写的问题,现在应该重新思考写什么。我觉得现在的大问题依然是怎么写,我们已经在写什么上浪费了太多时间。怎么写决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不是说你写了民工就了不起,也不是说你写了小资谈恋爱就很丢人,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能力把我们现在极为混杂艰困的精神境遇写出来,写出纵深和背景、肌理和脉络。
2005年看了一本加拿大的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看完了很感慨,一个少年和一头老虎在海上漂着,写得森严壁立,全球化背景下人的几乎所有精神疑难猛烈浩大地扑过来。看完了人家再看自己,我觉得靠写什么根本救不了我们,我们的精神空间其实非常狭窄,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他的境遇和经验的研究远谈不上深入。另外,大家老是说,到这一代作家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看根本没解决,中国文学在整体上依然是技术贫乏。
洪治纲: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里面,私人化的问题并不是特别明显。私人化写作与个人风格是有区别的。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更看重个人写作的不可替代性,他们的主体意识非常强,不会轻易地认同某种思潮或某种集体意识,而是要寻找自身的审美优势。尽管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和文化记忆非常相似,甚至他们所汲取的知识素养也大同小异,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那样过度地迷恋自身的生命体验,也没有专注于某些过于狭窄的经验空间,除了林白和陈染的早期作品有些个人化意味,大多数作家更强调自己的审美风格。像东西的喜剧化,毕飞宇的力度感,艾伟的纤柔感,韩东的写实化,林白的灵性化,李洱的反讽感……都不一样。至于他们是不是走进了某种“窄门”,现在还很难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说,判断一个作家是否陷入“窄门”,主要是看他是否以迷恋的姿态进入了某种经验性的个人空间,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自拔。它更多的是针对表达对象的局限性,而不是话语的审美风格。当然,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还普遍地存在着缺乏一种大格局、大气势、大胸怀,或者说他们还缺乏一种对大格局大气势的控制能力,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手笔”。所以,他们在书写大气势的作品时,会更多地谋求技巧上的支持,像《花腔》就非常明显。从“窄门”走向“宽广”,并不是取决于叙事智慧,而是取决于创作主体的精神位格和卓而不群的思想胸怀,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只有创作主体的“心源”博大,才能“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才能找到写作的“宽门”,也才能创作出具有丰沛意蕴的深邃之作。
汪政:问题确实有非常复杂的地方,文学到了六十年代这一茬,个人化才被真正地重视起来,他们把现代文学的部分中断的传统接续上去了,使得文学的表达更加个性化,它们从性质、功能诸多方面重新定义了文学,比如文学不能仅仅是一种代言,文学是“我”的创作,而不是我们的“创作”,“我”是不可取代不可重复的等等。但不能因此将这一点绝对化,绝对化就会走向一己之私,走向自恋与封闭,“我们”不能代替“我”,但“我”也不能取代“我们”,更没有权利强迫“你们”与“他们”,私人化写作在根本上已经部分利用了公共话语传播资源,挤占了公共话语空间,这同样是强迫,是霸权,它伤害了别人很大的利益。
四、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与长篇小说创作文体
朱小如:虽然从现象上看长篇小说创作的文体更趋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有意识的审美理想追求,往往有时会无意识地增加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以莫言、贾平凹、刘醒龙等一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民族历史文化本身的丰富资源利用和相对稳定的中国式(地域方言、民族戏曲、民间传奇等等因素)叙事的建构。这也使得当前长篇小说在“自然长度”上的扩展做得比较成功,像托翁、陀氏那种单纯的从“人物深度”上来完成长篇小说的毕竟稀少。我的问题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如何接续前辈作家们的创作脉络,或者如何另辟蹊径?其次有无可能真正的建立起像汪政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的长篇审美理想?
洪治纲:文体的多元化是文学创作的总体趋势。比如近年来,我就曾注意到,很多长篇小说都在进行文体上的探索,像孙惠芬的《上塘书》对地方志结构的袭用,刘恪的《城与市》在跨文体上的高度整合,韩少功的《暗示》对散文随笔的吸收,李洱的《遗忘》对历史考据学的渗透,刘震云的《一腔废话》对戏剧模式的运用,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对新闻记录体的沿袭,包括莫言的《檀香刑》对猫腔的引鉴等等,都折射了一些作家对文体意识的自觉。但是,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尤其是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不少都已视现代主义手法为惯常叙事技能,当他们在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创作积累之后,应该说,他们已感觉到了现代或后现代主义技术在长篇小说中的某些缺陷,特别是对人物形象的疏离。所以,我发现,他们在近年来的创作中,开始普遍强调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故事内在的丰实度,强调细节的饱满和鲜活,强调对叙事说服力的构筑等等。当然,如何向经典作品汲取营养,努力在长篇中塑造出具有经典意味的人物形象,还需要一个过程。
李敬泽:文体问题是个叙事难度问题。地方志、考据、新闻体、随笔等等,当然很好,但我觉得恐怕常常是皮相上的功夫,有时候你会觉得作家之所以采取这些办法,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取巧,是为了降低叙事的难度。
你看看现在的长篇,视角偏僻、复杂而受限制的很少,除了天马行空的“大我”,就是第一人称“我”——刚才几位老兄谈“我”和“我们”,我没有话说,这样的问题我们谈了十几二十年,以后还可能再谈下去,但是,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个人化”了就纲举目张了,而且“个人化”也是个永远讲不清的问题,哪有纯粹的“我”啊?你用语言时就已经包含“我们”了。所以,这个问题谈到现在,我看除了让大作家自我神化、让小作家自我安慰之外,没什么特别重大的作用。
作家当然有“我”,但那是个行动着的我、认识着的我、体验着的我、想象着的我,是个有技术的我,是面对难度克服难度的我,甚至是个自我消灭的我,有没有“我”得写起来看,否则都是白说。在写作过程中,他要解决的决不仅仅是我是谁,更是我应该是谁和可能是谁,就叙事角度而言,你只会依靠无所不知的不具名的“大我”或一个独断专行自我阐释的“小我”,这说明你那个“我”贫乏无能。
刚才大家都说到“窄门”,那是余华引用《圣经》的话,我觉得他说得很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了自以为是的“我”,却懒得去找“窄门”,懒得去找进入世界的独特的、有难度有限制的路径,结果还不是都走到宽门大门去了。
在这个时代,宽门大门都让报纸电视等等占去了,小说家是窄门最后的守护者,他在寻找进入世界的秘密路径,他不让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因单调而干涸,这个路径在哪?我看首先是角度问题,世界在什么角度下展开,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面貌,决定这个故事是个什么样的故事,作家有没有能力找到偏僻、复杂的角度,有没有能力克服困难让这角度充实起来,让世界焕发出独特的光辉,这是比文体问题更为根本的考验。
朱小如:近些年来,受文化市场的影响,不少出版社如春风文艺都在纷纷推出《高跟鞋》之类的小长篇。我记得汪政比较反对走市场的“小长篇”,似乎正是这样的“小长篇”败坏了长篇小说的传统审美。
汪政:我是反对小长篇的,在文体上我是比较保守的一个。短、中、长篇,尤其是短篇与长篇的历史比较长,也形成了有大量经典支撑的审美定律,这是文学史反复淘洗、筛选、积累的结果,轻易动不得。作家应该有文学史意识,对经典要有敬畏之心。小长篇是什么呢?是中篇的加长。中篇本来就是一个新兴的暧昧的文体,还不成熟。为了适应现在刊物的需要,再加上影视化写作的影响,就有了现在泛滥成灾的小长篇,它使许多本来不能从事长篇写作的人得以混迹其中,败坏了传统长篇的形象,使得传统长篇的许多审美特性与审美功能难以为继。复杂变成简单,丰富变成单薄,深刻变成肤浅。许多技巧以及赖以支撑的美学表达也成为不可能,比如描写,现在描写几乎难有立足之地,小长篇的篇幅限制太大了,哪里还有时间去描写,只能是叙述,叙述,再叙述,一路狂奔而去,这实际上是文学在图像时代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字优势。小长篇的问题很多,长度不是问题的全部,但许多问题却因长度而起,前几天,林建法来南京,我们还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莫言在大连会议上也发表过类似的感想,并将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刊发“捍卫长篇的尊严”的文章,一个对长篇缺乏了解的人是不会有这样的意识的。
洪治纲:小长篇的创作情形,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里不是特别的多,但在七十年代作家群里却普遍得到了认同。所以,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尤其是一些女作家,他们绝大多数小长篇都是不成功的,或者说,只是一种时尚类的消费产物。我也不太赞成所谓的小长篇,它给人的感觉是迎合当代文化的快餐消费心理,只能适应于简单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不是真正的长篇写作目标。所谓长篇,其长度主要取决于人物关系的安排和人物命运的走向,取决于故事的历史涵盖面和它的时空维度,取决于作家需要表达的丰富和多向度的人生思考。从常理上说,一部长篇所要表达的应该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生活,过度的简约化处理,要么是作家的审美思考不深厚,文本驾驭能力不够,故尔投机取巧绕道而行;要么是原本就是一个短篇或中篇的构架,作家主观上刻意注水而成。
汪政:治纲刚才的梳理是准确的,而且给了我们信心,我们确实有好长时间不太关注长篇的文体艺术了。长篇的“道场”是非常大的,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可能,其他的文体可以方便地进入,它不会给人挤占的感觉,现代美学也十分宽容,文体的界限变得十分富有弹性,柔性化了,另外,长篇的丰富复杂也需要变化、杂糅,它不仅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可惜这一点未能被更多的作家认识到。我之所以反对小长篇,也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六十年代作家也有不少写过小长篇的,即使从他们的自身来作比较,也是逼仄而单调的,比如江苏六十年代作家荆歌、罗望子、王大进,都吃过小长篇的亏。长篇的长度确实是一个不可一概而论的问题,多卷本好象显得有些古典了,似乎确实不宜多。许多人对长篇是有心理长度的,飞宇的感觉是三十万字左右,他甚至认为现代的小说已将古典时代许多长篇的难题解决了,不需要那么长了。这个说法表面上是有趣的,但又是可疑的,让人觉得小说像电脑,随着材料与技术的革命,存储量越大,体积越小,份量越轻。但小说的材料还是文字,技术也不是硬性与唯一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是史诗性的,汉译本也就二十几万字,但也只能是小说现实之一种,反正不管什么时候,丰富多样与相当的长度是我对长篇的基本的期待。
李敬泽:小长篇的问题很复杂,它涉及到我们经验和体验的自然长度,比如写一百万多万字的长篇多半是要以历史为后盾,因为历史支撑了这个长度,否则你写2000到2005年间的事也写一百万字试试。“80后”的长篇差不多都是小长篇,他的经验的自然长度就是那么多,《红X》写得长一点,那是因为它比较宽。
但由此又有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失去了自然长度的支持,我们为什么就写不长?或者说为什么写不宽写不厚写不重?小长篇是不是表明我们在简化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无法为这个经验提供纵深和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小长篇是有些怀疑,它很像是艺术上的权宜之计。当然也不能说写十二万字就不好,写三十万字四十万字就好,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维持对“重”的把握。自昆德拉搞出一个不可承受之轻,卡尔维诺搞出个“轻逸”,“轻”的哲学和美学在中国就大行其道,它成了小资和流行时尚世界观的核心配备,昆德拉就是个小册子小说家,你很难想象他能写四五十万字,他的气力和眼光就那么长,卡尔维诺的轻逸本来不错,举重若轻,是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橘逾淮北则为枳,到我们这儿,轻逸就变成了轻浮、轻易,变成了飘,所以,问题不在写多长合适,而在我们是不是要维护对重、对宽、对驳杂与丰富、对深邃与困难的体认和表现。
(一)(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