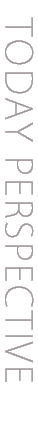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北岛及其《今天》诗派
李劼
不乏有人谈论北岛,北岛的诗歌已经有几十种译本。至于《今天》杂志的传奇,也是已经有人作了专题讲说的。我只能从我所认识的北岛说起,说到我对《今天》的印象为止。
我与北岛相识很晚,晚得让我和北岛全都惊诧不已。二十七年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非常认真地抄写过北岛的诗歌,当然还有舒婷等人,那群被称作朦胧诗人的作品。其中,我最为认同的是北岛。他写遇罗克的那行诗句,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不去: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北岛的诗歌本身,其实就是从弹孔中流出的黎明。其中,凝结着郭路生的悲怆,遇罗克的英勇。虽然北岛曾经声称: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我最早的诗歌评论,评说的就是北岛舒婷顾城的诗歌。其中,以北岛居首。这并不仅仅因为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人之中,北岛的影响力至今首屈一指,而更是由于我不知为何,特别共鸣北岛的诗歌。
在我热衷于八五年以后的先锋小说之后,北岛不知不觉地淡出了我的视线。当我流亡到美国之后,听到有关北岛的传闻,几乎全都是负面的。那些传闻让我感觉到,北岛已经不是当年诗歌中的北岛了。我为此在备忘录的初稿中,对北岛写过一些相当愤怒的文字。
从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歌,到在纽约与北岛相遇,整整隔了二十七年。有趣的是,与北岛相遇之后,我发现又回到了当初对北岛诗歌的印象。依然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仿佛一张对比鲜明的黑白照片,伫立着一个不屈的身影。与诗作中的激昂不太相同的是,北岛说话时的沉着。听上去不像个诗人,而像个无数次诗歌运动的组织者。
这真是个奇妙的反差,在诗歌中激情澎湃的北岛,在现实生活中恰好相反,冷静理性,宛如学者。虽然北岛连大学本科的学历都没有,但他却在欧美许多大学里先后教了如许年的文学课。他的一本随笔,《时间的玫瑰》,如同一部正儿八经的学术论著。从诗作的分析到诗人的故事,从诗人的个性到诗歌运动的发生,连同其历史背景和年代标记,历历在目。思路清晰,条理分明。甚至连那些诗歌在翻译成中文过程中的一些失误,都被一一指出。这本书说是随笔,其实又是评论,还是条不紊的叙事,叙述成一部由九个诗人生涯组成的小说。不仅生动,结构也十分精致,经常可以看到蒙太奇跳跃,从异国诗人的传奇突然剪切到北岛自己的亲历故事。最后一篇叙述狄兰椰城迄答满M竟然采用了倒叙手法,从诗人之死写到其童年记忆。
以前,在北岛的爱情诗歌里,曾经读到过他特有的细腻。这样的细致,也同样见诸北岛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北岛对他人的阅读和理解。在我此前认识的诗人当中,好像只有韩东具备如此品性。诗人大都以自恋为其特徵,有的甚至自恋到了仿佛不自恋就不是诗人的地步。北岛是很少的例外之一。
阅读随笔《时间的玫瑰》和阅读北岛的诗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诗歌里的北岛里是个充满自由精神、阳刚之气十足的北方男子,好像随时准备赴汤蹈火。而随笔里的北岛,却像一个事无巨细全都乐于躬亲的南方女子,一个优雅、细致地从事园艺劳作的园丁,悉心栽种和照料着那片叫做诗人的花草树木。他在后记中提到,其中所有篇什,或者说一草一木,其第一个读者,都是他的妻子,甘琦。
我所见到的甘琦,是个以尽可能女性的风格,在言行之间掩饰其男性豪迈的北方女子。按照某种阴阳互补的原理,我相信,北岛之于甘琦的吸引,与其说是北方气派的诗歌,不如说是南方格调的随笔。以此想像甘琦之于《时间的玫瑰》的阅读,是一幅相当奇妙的图景。我猜想书中有些细节,可能掺有甘琦的内助。我后来问过北岛是否如此,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无论作为二十世纪西方诗歌阅读的入门,还是作为二十世纪西方诗人的研究,《时间的玫瑰》都提供了一个富有独创性的文本。文学评论最忌讳的是学究气。尤其论说诗歌,没有洞微烛幽的功力,成千上万的文字,顷刻间成为一堆废纸。能够让人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这般挑剔的读者。我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随着作者走进了那些诗歌,走进了那些诗人各各相异却又息息相通的精神世界。不知为什么,阅读《时间的玫瑰》,让我时时产生写作小说的冲动。虽然此书写得相当冷静。甚至,过于冷静了。尤其是比之于俄国流亡思想家之于俄国文学的激情,那种《旷野呼告》式的深邃苍茫,北岛的描述,线条清晰而纤细,色彩微暗而清淡。倘若那些俄国流亡者展示的是原始森林,那么北岛的浪子情怀所构筑的,则是一个优雅的美丽花园。
北岛仿佛一个天生的流亡者,自从1989年发起释放政治犯的那个签名信之后,便开始流亡,至今已经历时将近二十年,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可是当他坐下来与人谈话的时候,却丝毫没有行色匆匆的急迫。由此,可以想像他当年是如何相当从容地写下一行行充满叛逆精神的诗句的。从容的叛逆和焦灼不安的叛逆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区别。基于不认同专制的叛逆是从容的,比如林昭,比如遇罗克。由嫉妒而生的叛逆是焦灼不安的,比如孙中山,比如毛泽东。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言下之意很清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某种意义上说,北岛早年的诗歌,是林昭的续篇。虽然北岛当年写诗的时候,并不知道林昭的故事。但林昭在黑暗中划亮的一根火柴,在北岛的诗歌里变成了一把通明的火炬。北岛的这几行诗句,就像是献给林昭的颂词:在黑暗中划亮火柴,举在我们的心之间。你咬着苍白的嘴唇:是的,昨天??(《北岛诗选》)
昨天的林昭如同遇罗克一般地倒在星星般的弹孔中,带着普罗米修士盗火之后的微笑。那样的微笑由北岛作了承继:从微笑的红玫瑰上,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北岛《北岛诗选--微笑岁楫□星星》)北岛不仅采下了歌谣,而且还作出了那个烩炙人口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求求《北岛诗选求求回答》
倘若说,林昭是中国专制历史上的自由女神,那么北岛的诗歌则是自由女神举起的那把永恒的火炬。自由,乃是北岛诗歌的灵魂,也北岛与生俱来的个性。我对北岛及其诗作的内心认同,就在于此。心灵因为自由而息息相通。彼此第一次见面,就投契得毋需赘言。彼此没有同是天涯流落的感觉,只有因为共同的自由脾性而致的投契和相通。
百闻不如一见。与北岛的会面,使很久以来一直在我耳边流传着的种种传闻,烟消云散。彼此谈了很久,谈了很多。一次不够,再一次,又一次。耳边时时回响着他的《结局或开始求求献给遇罗克》。这首诗其实也同样献给林昭以及和林昭一起倒下的《星火》文学社那些英勇无畏的盗火者。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在我听到的有关北岛的传闻中,其中不少跟诺贝尔文学奖有关。我当时觉得,北岛不必那么在意这个奖。我如今更觉得,北岛根本不必在意这个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喜欢把桂冠戴在某个陌生人头上。比如以戴在赛珍珠头替代戴在伍尔芙头上。北岛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对于在专制黑暗中走投无路的人们的鼓舞,对于普天之下所有向往自由的读者的意义,并不因为诺奖的有无而改变。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几个学者教授的文学爱好,跟真正的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林昭,并没有得过什么诺贝尔和平奖,但林昭跟任何一个荣获该奖的伟大人物相比,都毫不逊色。当文学走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那样的山巅,无论什么奖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自由的黎明,因为是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的,所以站在黎明中的北岛,完全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专制的黑暗没有将北岛给淹没,艰辛的流亡也没有使北岛日渐消沉,诺奖的有无当然更不会给北岛增色,或者,减色。
北岛说起在流亡中倒下的顾城,语气十分沉重。一再对我说,事情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他说,也许有位朋友关于顾城之死的评说,比较准确:一条小河向往着大海,可是真的流到大海,却又想退缩了。悲剧于是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诗人的心路历程,就是从叛逆到流亡。比起当年的《星火》诸君,《今天》诗人显然要幸运得多。这不仅在于,《星火》诸君划亮的不过是一根微暗的火柴,《今天》诗人点亮的乃是一炬火把;还在于当年的存在以生存的终结为代价,而《今天》的存在却并非没有求生的希望。其中,除了倒下的,消沉的,或者高升或者消声匿迹的,还有继续挣扎的,还有像北岛这样顽强地存活下来,并且顽强地把《今天》一期一期地出到如今。这是一种罕见的生生不息。当我听北岛说,《今天》依然还在办的时候,不由唏嘘了一声,简直是个奇迹。
今日的诗人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专制的黑暗,还有商业文明的冷漠。大洋的一边是唯物主义的盛宴,大洋的另一边是科技文明的疯狂。诗歌,自由,心灵,存在,完全成了被边缘化的陌生世界。就诗意的存在而言,大洋两岸的世界全在发疯。而对那个发疯的世界来说,依然在写诗依然要存在的人们,才是真正的疯子。当今的世界,不在于有没有疯子,而在于究竟谁是疯子。
当然,人们不会理解什么叫做疯狂,什么叫做自由。一如人们阅读北岛的诗歌,总是怀念早年的激情,难以进入他后期的美学追求。事实上,假如诗歌不止是时代的号角,而更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北岛的后期诗歌更为走向诗歌本身。虽然北岛早年的诗歌是令人怀念的,但这并不能因此构成北岛诗歌人写作的一道高墙。当诗人越来越走进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诗歌所出示的审美景观,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由时代而诗人、由历史而诗歌的变换。这里例举其中的一首,对应早年《回答》那样的激昂。
给父亲
在二月寒冷的早晨
橡树终有悲哀的尺寸
父亲,在你照片前
八面风保持圆桌的平静
我从童年的方向
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
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
你放牧乌云和羊群
雄辩的风带来洪水
胡同的逻辑深入人心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掌中奔流的命运
带动日月星辰运转
在男性的孤灯下
万物阴影成双
时针兄弟的斗争构成
锐角,合二为一
病雷滚进夜的医院
砸响了你的门
黎明如丑角登场
火焰为你更换床单
钟表停止之处
时间的飞镖呼啸而过
快追上那辆死亡马车吧
一条春天窃贼的小路
查访群山的财富
河流环绕歌的忧伤
标语隐藏在墙上
这世界并没多少改变:
女人转身融入夜晚
从早晨走出男人
同样是那个生他养他的城市,同样是那个弃他离他的国度,同样是亲近而遥远的亲人,北岛的晚期诗歌,呈现了与早年很不相同的意像。时代成了景深,而内在的感受被置于了诗行的前台。倘若有人将此称为知识分子写作,那么我宁可以零度写作命名之。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北岛的另一首诗,《零度以上的风景》:是笔在绝望中开花/是花反抗着必然的旅程/是爱的光线醒来/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
但我也同样注意到,北岛在这首诗歌里流露出来的倾向: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这句诗的潜台词,丰富而微妙。须知,北岛的父亲乃是一位共产党人。北岛的这声自白,虽然并非是对专制的认同,却是对与共产党有关的信仰的一个下意识回归。毋须讳言,北岛在长年的流亡生涯里,建立了他的左派信仰。那样的信仰跟共产党的革命和专制,并不是一回事。那样的信仰有点像青年马克思的自由主义热情。虽然共产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已经结束,但那样的左派自由主义热情,却在西方至今犹存。西方有不少在人格上无可非议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出自善良和平等的理念,出自由此生发的正义感,坚决不认同资本主义和财富巨头。这和中国有些新左派以冠冕堂皇的左派理念掩饰他们卑下的生存动机、摄取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北岛的左派信仰和左派理念,接近西方知识分子的品性。虽然我在理念上并不认同北岛,但从我认识他之后,就将他视作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友情是大于理念的。即便是不同的信仰,都可以互相容忍,更何况彼此之间,多少有些惺惺相惜。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