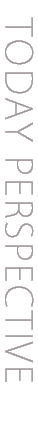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林白:一九七五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木叶
“王安忆笔下的人物是很有分量的思想者,我这里没有思想者”
木叶:李飘扬、安凤美等是真人吗?小说写到的人有没有来认领自己的故事?
林白:上部本来是前言,是以回忆录的手法写的,里面的人80%是真的,也有一些不是,李飘扬是以我为原型的。下部就是小说家言了。
估计会有人来认领。写的都是很好的朋友,充满了善意,充满了对时光的……也不能说是痛惜。他们看到了自己过去的身影也会跟我一样百感交集。
虽说上部是回忆录式的写法,但是我写完以后拿以前的日记来看,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个记忆,不见得是真实的,在小说里是一种重构。书中的一个人物吕觉悟的原型正好11月中旬来北京,她是我小学同学,跟我回忆童年。比如她说我小时候翻墙的事,我根本不记得了。她印象中的我跟我记忆中的我也不一样。
我小时候非常野的,翻墙,上树,下河,偷人家的水果,把公园里的花都摘光了吃花心里的甜水,还玩火,诸如此类的。我记得上树,还记得被狗追得掉进石灰池里,全身沾满了石灰,她就陪我到河里去洗。但是有些事我完全忘记了,一点印象都没有,她还记得很多细节。
所以我怀疑这个所谓回忆录(其实它就是小说的正文的组成部分,说是前言,它也不是真的前言,声称是回忆录,它肯定也不是真正的回忆录)的真实性,跟自己的日记不一样,跟同学的记忆也不一样。虽然我5分钟前告诉你是80%真实,但过了5分钟我这么一回顾一梳理,发现肯定不是,也说不清是百分之多少真实了。
木叶:你说这部小说“如果七十年代写就成了伤痕文学,八十年代写就成了寻根文学,九十年代写就成了新写实文学。”如今2007年写出来算是什么呢?
林白:这就是我个人的东西了。因为以前年轻嘛,容易受到潮流的左右。那现在比较老了,不那么容易受到潮流左右,就根据内心的召唤。我回了一趟老家广西北流,百感交集,真是为自己在写。
木叶:刚才你说到“百感交集”,我想起《红楼梦》结尾的“似喜似悲”。
林白:百感交集就是一言难尽吧,没法很清楚地说出。
木叶:同样写的是文革,王朔《动物凶猛》,姜文改编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致一九七五》有一点儿怀念或敬意。
林白:“致”也不能说是敬意,就是从这里到那里,写给那个年代的,主要是把那个年代当成一个有生命的人,是写给这个人的。任何年代,人在其中,未必觉得是苦难的,像《阳光灿烂的日子》。“走资派”被吊死,他苦难,但是小孩不上学,不用背书不用学钢琴不用学英语,自由得很。
木叶:还有一个是王安忆今年写的《启蒙时代》,也是写了很多人,手法有一定的接近。
林白:嗯,我觉得很不接近,她写人物很深入,她是思想者。王安忆笔下的人物是很有分量的思想者,我这里没有思想者。
木叶:她写的是1960年代中后期,你写的是1975年前后,为什么相差较大?
林白:反正我在那个年代的生活中没有接触到思想者。王安忆是在大城市,相对于广西,上海肯定是大文化中心了。然后还有她的出身,而像我是草根,家里除了医书、毛著,只有两本文学书,一本是《阿诗玛》,一本是诗集《红松》。周围没有出现过思想者,没办法把握思想者的形象。
木叶:小说里讲对你们班而言,搞化肥腐殖酸铵就像一个国家制造原子弹。还有狗说的那句话等,挺有意思。以前大家看林白的印象更多是唯美,幽默不是很显著,是不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呢?
林白:我现在觉得唯美挺无趣的,幽默更生动更鲜活,当然以前我的作品也有喜剧色彩,如《玻璃虫》。《致一九七五》后半部分幽默比较多,有一定的喜剧色彩,97年写的时候就想赋予喜剧色彩,有一些解构。上部《时光》没有任何喜剧的念头,即便小孩做游戏也学毛主席的话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那种幽默更多是隔了三十多年看的感觉,不是刻意的。另外呢,大环境主要是无厘头,是搞笑,我不是,不一样,要严格区分开来。
木叶:前些日子采访刘震云时他表示,很多悲剧仔细看都是由喜剧组成的。
林白:第一,文革不适合用唯美的笔调来写,第二,我这种叙述不觉得是受了大环境影响。我感觉到,文革中有另外一种东西:又喜剧,又荒诞,喜剧里有荒诞的色彩。这种调子,比我去声泪俱下地控诉一个时代,或是很沉重地反思,更贴近我的本性。
“还没有一个能耐下心来把我的作品理出一条线的导演”
木叶:里面提及的电影很多,是怀旧还是为了那种现场感?当下的电影看吗?如《色,戒》《太阳照常升起》。
林白:不是怀旧,是一种现场感。革命歌曲、电影歌曲当时都渗透到日常生活里面了。当时没有什么娱乐,一个电影一个样板戏出来,一个人看几十遍,都成为自己本能的话语了。
你说的这两个电影都没看,有碟了吗?哪天去买来看一下。
木叶:余华苏童莫言等都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我还真不清楚你有哪一部改编过?
林白:没有任何一部。主要是没有对我的作品特别有兴趣的导演。
可能人家都认为我的作品不适合改编成电影,其实也未必,你看《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都被改成电影了,任何东西都能改成电影!像于坚的长诗《零档案》牟森都给改成了舞台剧。有什么不能改的?都能改。就是还没有一个能耐下心来把我的作品理出一条线的导演。我也不想这个,干嘛啊,多累啊。而且小说是我自己的,电影是人家的。
木叶:小说中同时还有大量革命歌词,我想知道对于今天的年轻歌星像李宇春、周杰伦,你听吗?你日常的娱乐是什么呢?
林白:都不听。因为我要大量睡觉,我睡眠质量很差的。还要大量走路,所谓徒步,剩下就没什么时间了,我又要整理旧的东西。
有各种各样的作家,我是一个挺自我的作家吧。
木叶:不考虑读者?
林白:你很难考虑,因为读者你是不知道的,而且市场是变幻莫测的。别说你要取悦读者了,就连你要取悦一个恋爱对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就断了这个念头,不要取悦读者。
写作的时候我喜欢心无杂念。
比如市场怎样,读者喜不喜欢,火不火,能否成一部伟大作品,得不得奖,评论家会不会叫好,等等。这些都是杂念,所有杂念都是镣铐。等书写完之后,要面对出版和市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以前积累下来的读者量使出版社愿意出我的书,这就很不错,像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她的《情人》出版之前的很多年,她每本新书只能印几千册,她六十多岁后才拥有大量读者。我相信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作家,但可能他写不到六十岁就放弃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我的读者是在意的,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本这么厚的《致一九七五》才得以顺利出版,否则是不可想象的。但如果我的书卖个几十万,可能也是荒诞的。
我相信我不会是一个大众作家。
木叶:我看到你给女儿买过郭敬明的《幻城》,你对当下的年轻作家有什么交流和关注?
林白:一个是我没什么交流和关注,第二个是我得警惕这样的话题。我听说《幻城》印了几百万册还是多少,确实很奇怪,有这么多人爱看,就给她买来看看。后来她好像也没看,书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女儿还挺想当批评家的,我就说那你批评一下郭敬明,她说她不批评,她还不愿意批评,她觉得郭敬明还没够她批评的那个级别。
木叶:那你自己对新人是怎么看的呢?像安妮宝贝、张悦然、韩寒……
林白:新人越多越好。原来我不知道,都说文学市场萎缩了,后来据批评家李敬泽说你看看网上,文学作者上千万。我一听这么多,哪里萎缩了?
一般他们本人或出版社把书送给我,我就会翻一翻。最好谈到具体的人不要涉及人家,因为新人的读者群都很大,好像我拿人家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最好不要说。
“我就特别怕问我对‘80后’有什么看法”
木叶:“当代所有散文,基本上都不能算真正的文学作品!我应该少出版散文集。真的很微不足道。”你真是这么看待散文的?我听说你特别喜欢胡兰成。
林白:这个是比较偏激了,属于话赶话,不是负责的态度。主要是指媒体的散文,还比如我的应景之作啊,我觉得连后记都算应景之作。
“散文家”很难听的,写散文的朋友坚决反对强烈反对别人叫他们散文家。散文家特别不独立。诗人就是诗人,小说家就是小说家,哪有什么散文家?
胡兰成也不是光写散文,他还写史,他的眼光和底子在那儿呢。不能说他是专门写散文的。
木叶:小说里引了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还提到海子的“以梦为马”,你自己也写诗,写小说的你是怎么看待诗的?
林白:诗肯定是最高形式,确实可以这么说。诗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了,什么时候就没了。诗歌是很神奇的。
木叶:你不喜欢“女性主义”这个标签。
林白:哪个作家会这么傻,被一个主义所局限,被一个标签所局限,那傻到家了。不会这么傻的。
木叶:不光你受此影响,今年多丽丝?莱辛获诺贝尔奖时,女性主义的标签还是挺吃重的一个说法。她的《金色笔记》看过吗?
林白:我没看过,以前《金色笔记》这本书将译未译的时候,戴锦华就提醒我去看看,我就去找,没找到,出版了以后又专门去找过,还是没找到。我一直错过了莱辛。
木叶:她一获诺贝尔奖,书出了好几本,你有没有去“补课”?
林白:肯定《金色笔记》会买来看看,最近没时间去书店,等到闲下来,一定买一本。
木叶:那么前几年的诺奖评出来之后,你有没有一看究竟的心理?
林白:也还是有的,但也不见得就是想看他们为什么会得奖。有这么多人骂诺贝尔奖,但我觉得评的这些人也不是吃干饭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没那么急切,你想我去那么多次三联书店,库切的《耻》摆在跟前,就是没买。后来我去武汉,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就看不过眼了,说你连诺贝尔奖的书都不买,就给我买了一本。但我还是没看——书放在武汉那个家了,一直没去。
耶利内克《钢琴教师》,看了个开头就一直没看下去。
木叶:的确不必急着看,慢慢来。那么历次采访以来,有没有特别不想回答或是特别怕被问到的问题?
林白:我就特别怕问我对“80后”有什么看法。确实很难回答,而且我也没什么时间和机会看。你说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干嘛非要买他们的书来看呢?除非是买来给我女儿看。
木叶:去年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今年方方刚当了湖北作协主席,王安忆连任上海作协主席。你同一辈或稍长一些的女作家,当官的真是不少,你有什么想法吗?
林白:我怎么会有想法呢?我跟作协是很疏离的。这么多年我没有开过任何一届“青创会”,“中创会”也没开过,“作代会”基本上也没开过,作协的所有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等等等,一般人都会得的,我一个奖都没得过!
我的小说,选刊都不选的。所以我是一个反常规的作家,而且还是比较边缘或者是说双重边缘的作家,一个是市场反映不是很火,从来没有大红大紫,林白的书不是那么好卖的。再一个在作协系统,我也是比较边缘的,我怎么可能当主席呢?
木叶:那么我就想,真的边缘,咱就连作协都不入。
林白:但我不是那种真正的边缘,真正的边缘是完全没人知道的,完全在角落里写作。我是属于那种在夹缝里成长起来的作家,是两边的夹缝,在市场夹缝里,说林白的书不好卖吧,不少书店也还会进一些;作协系统呢,在北京我没当专业作家,外地作协还是容下了我。所以我这种人不可能有那种当官的身份……我跟人家不在同一个话语系统里。
木叶:前些日子采访马原,也说自己一个奖都没得过。
林白:我倒是得过一个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妇女闲聊录》,2004年。
木叶:这是媒体评的,不是官方的奖。
林白:官方的奖肯定没得过嘛……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觉得委屈,一点没觉得委屈。
木叶:很多读者看到署有林白二字的书就会看,这就可以了。人在夹缝中生长,你的文学梦或野心有没有,是什么?
林白:完全说没有也不真实,应该还是有的,野心就是希望自己一直拥有创作的活力,内心有生生不息的源泉,能够生长,慢慢地生长。
木叶:没有想写出一部什么样什么样的作品?
林白:我上面说过,写出伟大作品的想法是一种杂念,所有杂念终将是镣铐。所以我希望自己心无杂念地写作,既不要要求自己写什么史诗性的伟大作品,也不要写什么完美的作品,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写作。
《上海电视》
2007 12 11-13
(一)(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