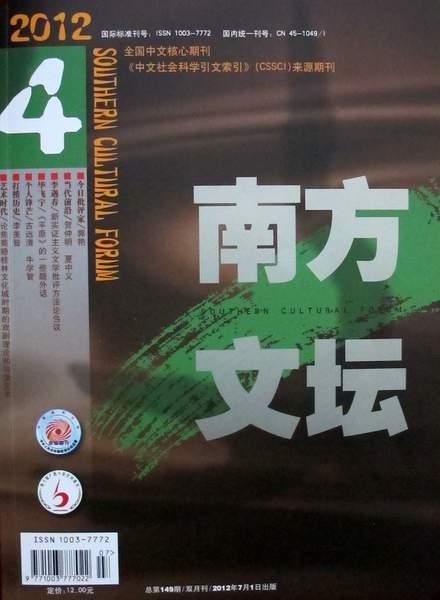[立此存照] 欧阳光明:骚动心灵的寂寞之舞——陈谦小说论
骚动心灵的寂寞之舞
——陈谦小说论
欧阳光明
[原载《南方文坛》2012年第4期]
陈谦是新移民作家群中一位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与其他新移民作家相比,陈谦对新移民所面临的外在困境关注得较少,而是直接深入到他们的灵魂世界,在现实和理想、理性和感性、家庭伦理和个体生命激情的冲突中,执着地探寻人的内在困境,并由此塑造了一系列寻梦者形象。随着创作的延续,陈谦又开始回望那段给每一个中国人造成心灵隐痛的历史:文革,试图为那些深受历史创伤的人寻找一条拯救之途。陈谦的小说,看似简洁,实则繁复,在文本结构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叙事智性。
一
对沉闷现实的反抗和超越,对理想人生的追寻,对自由的“灵性生活”的渴望,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构成了陈谦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从以笔名“啸尘”发表的处女作《何以言爱》到《望断南飞雁》等一系列的小说,陈谦几乎都在追问这一生命的困境——压抑的现实秩序与骚动灵魂相遇时所产生的矛盾,以及如何走出这一困境,获得一种激情飞扬的生活。陈谦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是女性,这可能与作者的身份有密切联系。这些女性,有些是美国“硅谷”中的成功人士,有些是迷失在异乡爱情中的追梦者,还有些则是不愿意生活在丈夫的羽翼之下,过宁静如水般生活的全职太太。她们都不愿认同现实,不甘心向刻板的现实生活投降,而是宁愿听从内心的召唤,追随骚动的灵魂,寻找一种能安妥灵魂的生活。为此,她们纷纷放弃安宁的生活,走上动荡不已、却也精彩纷呈的寻梦之路,留下了一个个为寻找梦想而不停奔波的身影。
由此,我们看到,在《何以言爱》中,无忧无虑的大院子弟钱莹,突然感到百无聊奈,甚至身心被空虚和寂寞所吞噬。为了改变这种生活现状,钱莹决定出国留学。在出国前夕,她又与勤威进行了一次耐人寻味的情感角逐。在《艺术家小猪》中,小猪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不拘一格,不惧世俗眼光的探视,为梦想坚持到底。《看着一只鸟飞翔》像是一则寓言,在梦呓般的叙述语调中,把主人公渴望飞翔的心,精妙地刻画了出来。在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面对“灵性生活”的召唤,迈出了稍显犹豫的步子。这一步给她带来了惊喜,也不乏沉重,甚至有些凄婉,但她并没有后悔这样的选择。对于苏菊来说,“灵性生活”携带的魅力太过强大,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指标,对此都无法产生免疫力。未婚夫利飞冷静而理性的生活态度,远远比不上感性、邋遢却激情飞扬、充满幻想的王夏。因为,“她喜欢的是有动感,有灵性,有激情的生活,而跟利飞在一起,她觉得总进入不了她所向往的那种境界。”[①]
相对于《爱在无爱的硅谷》情节的单线条演绎来说,《覆水》显得更为复杂一些,感情也更为深沉一些。美国人老德挽救了依群的生命,却无法安妥她那颗年轻的灵魂。肉体上的病痛,给依群带来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感,而心灵上的隐痛,才真正让她感到了地老天荒般的疲惫感,潮水般的压抑,足以窒息她重获新生的生命。依群几番努力,试图冲破这种无形的牢笼,但老德的“恩情”就像一个紧箍咒,将她死死捆住,再加上艾伦的理性退却,适时的提醒依群“我们的生活不在别处”,[②]依群虽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在现实与梦想的冲撞、感恩与生命激情的搏杀中消耗自己。这着实让人感觉到了她那颗骚动的灵魂,在寂寞之舞中的悲壮。
《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以决绝的出走,宣告人们应该遵循内心的召唤,去寻找那种灵性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在别处”。而在《覆水》中,依群带着家庭伦理的强大束缚和“报恩”的心理,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只能接受艾伦“我们的生活不在别处”的规劝。这种矛盾的认识让人泄气,甚至绝望。但这就是现实,或许只有经过重重矛盾磨练的生命,才更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尊贵和崇高,带着镣铐跳舞,会更加动人。在《望断南飞雁》中,这种“带着镣铐跳舞”的魅力,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南雁长期作为陪读夫人,家庭主妇,尽心尽力创造出一个温馨的家。但为了给自己一个重新规划生命的机会,南雁最终放弃了家庭的负担,孩子的拖累,在丈夫将要获得终身教授资格前夕选择了离开。南雁一直都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你要去发现它,完成它。”[③]正是这样,她才会对即将到来的“幸福”视而不见,在背后留下了人们嘲杂的叹息声。
如果遵从现实的评价标准,苏菊和南雁等人的追求无疑是“愚蠢”的,放弃“完美”的生活,追寻一个不确定的人生,最后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这不是愚蠢又是什么?但人的奇妙之处、人的高贵和可敬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没有为梦想而具有“飞蛾扑火”的勇气,如果生命的丰盈都要以现实中的量化标准来衡量,那么人的丰富灵魂和飘逸的诗情,将会退归为零。这样,生命将会凋零,灵魂也会枯萎,人最终会在简化的现实当中,无奈地走进荒凉的人性沙漠,走进“理性抵制了超越”这一可悲的境遇中。[④]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苏菊们的选择显得灼灼生辉。
除了对理想、灵性生活的追求之外,陈谦小说中的一些女主人公们,还选择了在爱情中燃烧自己。对于人类来说,爱情是美丽的,也是诗意的,它能给乏味的生活增加绚丽的色彩,给苦难的人生带来灵魂上的安慰。但它又是脆弱的,往往在残酷而僵硬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可能唯因其绚丽,才容易熄灭。如绽放在天空的璀璨烟花,瞬间留下冰冷的灰烬。人们可以为了爱情,寻找终身,也可以在现实面前,将其击成粉碎。在文学世界里,留下了太多爱的慰藉,也留下了太多肝肠寸断的斑斑眼泪。《残雪》中的丹文,曾经在爱情里找到了幸福,也承受了被抛弃时的痛苦。此后,她始终走不出爱情的迷局,最终在爱情的世界里迷失了自己。她只身来到北美寻找答案,却得到一个命丧他乡悲惨结局。《一个红颜的故事》中的朱颜,同样在爱情中体验到了火与冰的两重天,她也遭到了被抛弃的命运,只不过没有像丹文那样迷失,而是如凤凰涅槃般获得了重生。《谁是眉立》也是一个忧伤的情感故事。晓峰的离去,在可雯心里刻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成了心中的一个“结”。虽然可雯最终走出了“心结”,但还是让人们看到了她心底的忧伤。事业上,可雯和晓峰都是成功的;然而,在情感上,他们又是迷路的羔羊。
中篇小说《繁枝》叙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新世纪的“红颜的故事”。与丹文一样,在化学博士锦芯身上,再次重演了“红颜薄命”的悲剧。锦芯面对丈夫的背叛,在苦劝未果的情况之下频生杀意。丈夫死了,她也绝望地选择了自杀。被抢救过来的锦芯,不得不承受着器官衰竭和精神抑郁的双重折磨,还有FBI对她的追查。锦芯显然无法坦然面对这样的生命绝境,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她只能悄然而逝,留下“我是一只夏末的孤蝉”的绝唱。事实上,《繁枝》也是对《残雪》的一个呼应和扩写,两篇小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互文效应,并让我们看到了“丹文”另一种可能性的结局。在《繁枝》中,作者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命运发生逆转,如果被杀害的人是另外一个人,结局会怎么样?《残雪》中丹文被杀害了,叙事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凶手是谁,但从小说文本所提供的线索来看,我们分明知道,凶手就是丹文的前夫;在《繁枝》中,志达的死,也并非“生病致死”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次蓄意的谋杀,而几乎所有的证据,都在证明锦芯就是这个谋杀者。丹文被人杀害了,锦芯却是一个谋杀者。锦芯虽然活着,但活得并不愉快,始终被恐惧、孤独、凄凉的氛围所笼罩,最终还得面对法律的制裁。丹文和锦芯们的遭遇,让人看到了爱情的美丽与残酷。但她们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像堂吉诃德般冲向冰冷的现实,不惜用生命来追寻一个答案,又让人看到了女性的勇毅与坚强。
在上述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陈谦刻画了一系列女性追寻者的形象。她们或者在面临现实和生命激情碰撞时,听从内心的召唤,毅然走向远方;或者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守护一颗骚动而寂寞的灵魂;或者在爱情的迷局里,寻找不同的答案。这样的寻找,给她们的生命增加了斑斓的色彩,却不一定是成功的光环。苏菊们的追寻都不完美,但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永不停息的内心追求,以及渴望独立、自由的女性意识。和“五四”时期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相比,苏菊们的追求少了宏大的使命意识,少了社会和文化所赋予的诸多内涵,少了密不透风的文化压迫,少了经济上的无力感。她们是一群经济独立的女性,面对的是个体“灵魂的喧哗与骚动”,虽然也能看到家庭伦理对她们的束缚,但这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她们的反抗和寻找,和“五四”时期的新女性一样,从另一个层面,展现出女性生命的妖娆风姿。
二
对灵魂冲突、生命困境进行了一番探索之后,陈谦还开启了另一条小说创作的审美通道。她开始打捞往日的沉钩,向记忆发出邀约,回望历史,试图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渐行渐远的生命经历中,给人们提供“另一种文革的故事”。这主要表现在《特蕾莎的流氓犯》和《下楼》这两篇小说中。
其实,在此前所创作的那些小说中,陈谦已经语焉不详地对记忆中的“文革”进行了回眸一瞥,只不过都是寥寥数笔,或者仅仅是一个片段,很少在那痛苦的记忆里驻足停留。这些片段,包括《何以言爱》中对钱莹的大院生活这一背景进行蜻蜓点水般的交代;《覆水》中对依群的父亲跳楼自杀、母亲被下放养猪以及哥哥插队这些事件的惊鸿回眸;《望断南飞雁》中对南雁母亲的不幸遭遇的简单复述等等。此时,陈谦似乎在有意回避对这些苦难事件的正面书写,也可能是对这样的历史“不曾有过一点兴趣”,[⑤]所以她才会在交代人物背景的时候,觉得有助于人物性格的成长时,才匆匆写上几笔,然后迅速离开。这一情况,在陈谦最近的小说创作中,有了极大的改变。从《特蕾莎的流氓犯》开始,陈谦停下了奔跑的脚步,决定正视这段历史,“在很多人选择忘却的时候,我开始回望。”[⑥]
面对“文革”,陈谦机智的选择了“心灵创伤”作为切入口,她或者通过年轻人苦难的遭遇,心灵的巨大隐痛,来窥探时代的疯狂;或者通过“丈夫在‘文革’中自杀后”,“二十多年都没有下过楼”的老太太,来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是的,关注“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进而希望找到一条拯救之途,走出“文革创伤”,才是陈谦书写“另一种文革故事”的主题。
在《特蕾莎的流氓犯》中,年轻的劲梅和王旭东,在启蒙普遍缺失的时代里,既缺乏对爱的基本认识,也不知道尊重为何物。所以,当青春期苏醒的身体欲望勃发时,他们注定要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宿命般地把自己喜爱的人,推向了灾难命运的深渊。此后,他们带着深深的心灵创伤,奔走在各自人生的路途上。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把劲梅改成特蕾莎;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享受人们羡慕的眼光;甚至可以组建一个看似完美的家庭。但是,他们无法驱逐灵魂的重压,无法缝合心灵的创伤。在《下楼》中,“文革”中自杀的父亲,在丹桂心里刻下了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在解开“父亲之死”这一谜团的道路上,丹桂又从黛比教授那里得知了康妮的惨痛经历:康妮在丈夫自杀之后,躲进自己的小楼里,二十多年来不曾离开半步。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康妮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因为她的时间,永远地停止了,永远停留在丈夫自杀的那一天,静止在“文革”的时间中。她怎么也无法忘记那个血腥的场面,走不出惨痛命运留给她的“心灵创伤”。
时代从来就不曾停下飞奔的脚步,来抚慰柔弱悲泣的心灵。它用自己瞬息万变的面孔,把曾经有过的血腥和灾难,悍然留在了身后,强行挟裹着人们滚滚向前。喧嚣不已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催促人们遗忘苦难,遗忘创痛。然而,那些灾难深重的灵魂,又怎么能轻易竦身一摇,把重负抛弃?那种潜伏在心灵深处的创伤,就像“猛兽”一样,会时不时跳出来,把人们的身心撕咬得千疮百孔。这正如特蕾莎所说的一样:“它扣在心上,我一不小心,它就钳我的心一下,生疼生疼,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它又像一个怪兽,伏在道旁,可能在你人生最得意的时刻,冷不防跳出来偷袭,让你的自尊瞬间挥发。”[⑦]该如何走出心灵的困境,弥合“心灵创伤”,把灵魂从灾难深重的深渊里拯救出来?这是陈谦在这两篇小说中试图回答的问题。陈谦认为,要想修复心灵的创伤,就必须直面心灵的困境,在道歉和忏悔中,驱逐心魔,拯救灵魂,从而获得一个再生的机会。而不是把曾经的灾难性错误推给时代,让时代这个无名的主体,成为制造灾难的唯一替罪羊。所以,在《特蕾莎的流氓犯》中,特蕾莎一直在寻找她的“流氓犯”王旭东,希望当面说出她的忏悔;王旭东也选择了研究历史,撰写了一本记录“每一个人的文革”的书,希望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以此来告慰在“文革”中受到创伤的灵魂。可是,作者也清醒的意识到,忏悔是需要勇气的。可这样的勇气,几人能有?事实上,这些芸芸众生,大多都选择了遗忘;或者以“向前看”为借口,把创伤深埋在心灵深处的黑暗里,永远不再碰触。遗忘和深埋创伤,并不代表灵魂的重生。要想走出创伤,获得灵魂的再生,就必须迈出这一步。虽然“它不过是形式。但形式很重要。不然他不能完成那个仪式,越过那道坎。”[⑧]
忏悔和道歉,与法律上的惩处无关,也不是要迫使经历“文革”的人认罪。它关乎的是灵魂上的事,与道德和良知相关。一个真诚的道歉,一声诚挚的忏悔,虽然不能更改历史,也不能避免已经犯下的罪孽。但它能让人勇敢的面对心灵的黑暗,给扭曲的生命换来生机,给苦弱的灵魂带来些许温暖,给破碎的心灵带来几束真正的生命之光。
陈谦说,“《特蕾莎的流氓犯》记写下的是我的叹息。”[⑨]事实上,《下楼》也是一声沉痛的叹息。这是面对心灵创伤的叹息,是面对遗忘的叹息,是对放逐灵魂的叹息,也是对“文革”时代缺乏启蒙的叹息。只不过,陈谦的叹息,把血泪现场有效地隐藏起来,它看起来虽然不那么暴烈,但却像在地下涌动的炽热岩浆,随时都在伺机爆发。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轻击重”的叙事方式,这种“对‘文革’历史的尖锐与沉重进行了若隐若现的表达”,[⑩]达到了“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11]读来让人震惊不已。
三
在当代小说的写作中,智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不但能直接彰显出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叙事的成败。这是因为,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再满足于一个完整的故事,他们希望在审美接受的过程中,得到比故事本身更多的东西,在“有意味的形式”里,进行沉思和玩味。当卡夫卡的小说面世之后,人们大感震惊,不由得发出“小说还能这样写”这样的感叹;卡尔维诺也一直致力于用一种“轻”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沉重。米兰·昆德拉主张用一种轻浮的形式,来表现他探索沉重世界的雄心。“将问题最严重的一面跟形式最轻薄的一面结合,这向来是我的雄心。”[12]并由此创造了“昆德拉式的讽刺和幽默”,风靡了整个世界;“黑色幽默”派,则把世界的沉重和荒诞,用一种“含泪的笑”表现了出来,在嬉笑怒骂中给人的灵魂一记重拳。王小波逝世之后,“王小波门下走狗”纷纷冒出来,就是因为王小波的写作,饱含了一种极富创造力的智慧,让人无法抗拒。无需再举更多的例子了,上述现象已经有力的说明,智性写作是当代作家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它不但重要,更是基础。从上述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智性写作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的洞察力,也即发现和感知的能力,二是讲述故事的智慧,它包括语言的运用,视角的选择,结构的安排等。陈谦的小说,在结构上,表现出不凡的智性,它们看似简单,实则繁复。陈谦把她的思考,巧妙融合在两性的情感纠葛中。表面上看,她只不过是在书写男女之间情感困顿这一陈旧的话题,实际上,情感纠葛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结构策略,是一袭披在小说外层的“华丽外衣”,只有穿透这件“外衣”,才能看到小说的肌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陈谦的每一部小说,都具有相同的繁复性。她的《何以言爱》、《艺术家小猪》、《鱼的快乐》、《看着一只鸟飞翔》等,虽然有不少哲理性的思考,也有一些很精辟、独到的论断,但就其结构来看,还是显得比较简单。甚至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其结构也并不复杂,只是在单线条的演绎中,安排矛盾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而在《覆水》、《望断南飞雁》、《残雪》、《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楼》、《谁是眉立》、《繁枝》等小说中,陈谦那营构小说结构的天赋,就彰显出来了。和许多新移民作家一样,陈谦的小说,经常出现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时空跨度,使小说情节在两个不同时空中演进。而在这广阔的时空里,陈谦显得游刃有余,表现出处理小说时空的娴熟技巧。但更为重要的是,陈谦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艺术。她似乎对小说的“圆形结构”情有独钟,所以,在多篇小说中,都采用了这一结构形态。
在小说《覆水》中,故事以老德的死作为开端,以清理完老德的遗物,在母亲“你得多想想你自己了”的嘱托声中结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形结构。整篇小说虽然是一个“封闭的圆形结构”,但作者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又随着依群意识的自由流动,不断打破这种“封闭式”结构,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无限开放的独特特征。依群留在曾经和老德生活过二十多年的房间里,不断地回忆起人生中的风风雨雨。她的思绪一会儿回到二十多年前,再次体验那段绝望的日子;一会儿又回到有老德相伴的时光,细细品味他们之间的酸甜苦辣;一会儿又回到当下,感受到人去楼空的凄凉,期间混合着点点“解脱”的欣喜。种种情感纠葛、爱恨情仇,在巨大的时空交错中,被有机的安排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场。
《望断南飞雁》也是一个典型的圆形结构。叙事从南雁离家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前夕开始,到圣诞节清晨结束。故事的主体部分,着重叙述了南雁和沛宁的情感旅程和生活经历,以及南雁那颗渴望摆脱束缚的飞扬心灵。中间穿插了沛宁与王镭的情感纠葛,南雁母亲的爱情悲剧等。小说的“回闪式”结构和“现在——过去——现在”的时空交错,与《覆水》的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结构,使得小说的文本层面,出现了一种错落有致的层级效果,也取得了类似于音乐那种循环往复的韵味,延展和丰富读者的审美体验。
这两篇小说,如果从开头和结尾来看,时间跨度并不长。但是,在小说的主体部分,陈谦采用了类似“意识流”的写作手法,让主人公的意识呈自由流动状态,充分发挥联想和想象,在过去和现在的世界里来回穿梭。主人公一会儿回到过去的时光里驻足停留,追忆那段“逝水年华”;一会儿又回到现实世界,冷眼旁观。整篇小说的叙事,跟随这种自由流动的意识,收放自如,最后又统摄在“圆形结构”这一整一的形式之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从而使小说文本呈现出灵活多变、珠圆玉润的效果。
这种圆形结构所携带的圆润和完美,曾受到了很多作家的亲睐。深谙圆形结构之美的钱钟书,更是对此赞赏有加,他曾说:“窃尝谓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13]陈谦显然也对圆形结构这种优点深有体会,因此,才会在不同的篇章中,不厌其烦的采用这一结构。
除了“圆形结构”之外,陈谦还积极探索其他结构文本的形式。如《残雪》,就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把丹文“千里寻夫”的故事渲染得跌宕起伏。冰天雪地的寒冷,与丹文阴冷的表情和冰冷的笑容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特蕾莎的流氓犯》中,陈谦把主人公的遭遇,放在两个不同的场域之中:“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生活和“文革”之后的北美生活,而两个地域所对应的时间,则是过去和现在。作者这样安排,并不是要对比两个世界生存方式的优劣,而是想说明,那种在“文革”时期所受到的心灵创伤,即便经历了巨大的时空跨越,甚至是身份的改变,也不会自动愈合。唯有忏悔,才能重生。《下楼》采用故事中套故事的“套盒式”结构方式,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心灵中所深埋的“文革创伤”的普遍性。而且,这种创伤,已经通过代际传承的方式,延伸到不同代际的中国人的内心。更妙的是,陈谦将“文革创伤”纳入到整个人类的视野中进行思考。从而使得这一短篇小说,积聚了非常丰富的信息量。洪治纲就认为:“《下楼》是一篇充满叙事智慧的小说。它避开了对沉重历史进行正面强攻的方式,巧妙地通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与一位创伤心理学教授的短暂交流,缓缓打开了沉重而又深邃的历史之门,并让人们意识到灾难之后的余伤远未结束。无论是丹桂、杰里还是黛比,他们如此的关注人类的心理创伤,既是自救也是拯救他人,拯救爱。它将中国的‘文革’作为一种内心隐秘的创伤性记忆,扩张到世界性和世代性的命题之中,尖锐,缠绵,幽深。同时在叙事上,它又声东击西,化繁为简,耐人寻味。”[14]《谁是眉立》采用了互文的方式,将於梨华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牟天磊和眉立的爱情悲剧,有效地融入《谁是眉立》中。不愿意成为“眉立”的可雯,竟诡异般地获得了与眉立相似的命运,离开了自己心爱的恋人。而定居香港之后的晓峰,由于太太长时间在外经商,只好承担起照顾三个孩子的任务,这与眉立的角色也极为相似。由是,“谁是眉立”这一问题变得甚是可疑。可雯不想成为“眉立”,晓峰更不愿意承他与眉立有关。可事实上,他们都是“眉立”,是眉立命运的同路人。《谁是眉立》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所形成的互文效果,主人公相似的命运,隐喻了命运的轮回,取得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审美效果。《繁枝》则用相当简洁的笔墨,把家庭、身份意识、寻根意识、爱情命运、女性悲剧等问题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进行思考。故事从在美国读小学六年级的珑珑的一篇家庭作业——介绍自己的家庭组成和来历开始,牵出了立惠对自己的身份和家庭的追寻。在寻找的过程中,立惠联系上了三十多年没有音讯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锦芯,从而得知了锦芯的爱情悲剧和生存困境,并不由自主地被卷入进去。在这篇小说中,叙事者不断地改变着故事的走向,把各种不同的主题,在旁逸斜出的叙事中,从容地将之纳入进来进行思考。正如它的题目“繁枝”所显示的一样,如一棵树不断分叉,生长出新的枝干,最后形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陈谦对小说结构形式的探索和处理,虽然不具备开创性,但她将这些叙事结构融会贯通之后,极大地丰富了小说文本的表现形式,也有效地避免了手法单一的叙事困境,表现出良好的叙事智慧。
从崇尚个体生命追求到打捞历史沉钩,正视“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寻找灵魂的拯救之途,陈谦不但成功地开拓了创作视野,还给作品赋予了更为丰厚的内涵,显示了不断超越自我的优秀品质。而且,置身于不同文化冲突的场域中,不同文化杂交融合之后,有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一优势,对陈谦这些新移民作家来说,应该是一个远未开发出来的精神宝藏。
[欧阳光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
[①] 陈谦:《爱在无爱的硅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②] 陈谦:《望断南飞雁》,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③] 陈谦:《望断南飞雁》,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④]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⑤] 陈谦:《创作谈:另一种文革的故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第5期。
TAG:
标题搜索
日历
|
|||||||||
| 日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 1 | 2 | 3 | 4 | 5 | 6 | ||||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
| 28 | 29 | 30 | |||||||
我的存档
数据统计
- 访问量: 123081
- 日志数: 349
- 建立时间: 2008-01-03
- 更新时间: 2014-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