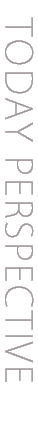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顾颉刚与谭慕愚──一段缠绵了五十年的情缘
余英时
我读顾的《日记》,从一九二四年开始,便为这个伟大的故事所吸引,以后《日记》中几乎随时随地都是谭的身影。顾为她写了无数的诗,也做了各式各样的梦,其情感之浓烈,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我所能看到的都是顾在《日记》中所提供的片面记载,对于谭的一方面,我几乎毫无所知;后来虽找到了一两条《日记》以外的资料,但都是关于谭在北大读书时期的政治活动。至于谭对顾得感情究竟是怎样回应的,她的内心又是如何感受的,我仍然是茫无所知。但仅从《日记》所见,谭已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现代女性,而终日在故纸堆中出入又复谨言慎行的顾颉刚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种,更使我为之挢舌不下。如果不将这一段情缘揭示出来,我们便不可能看清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来面目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载:
与介泉夫妇、缉熙及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陶桓连、谢祚茝、刘尊一、谭慕愚游颐和园、玉泉山,由彭君之兄及其同乡何君领导。上午八点一刻出门,下午八点一刻归,游甚畅。
颐和园最佳处为谐趣园,前数次所未到也。竹影泉声,清人心骨。予不到颐和园,已十年矣。今日与女子同游,颇感乐趣。必像我辈无玩女子之心者,社交公开始无可弊。否则但以女子为牺牲耳。
这是他和谭慕愚初逢之一日。五十四年之后他在此条之末题诗并跋云:
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偶展此册,不觉悲怀之突发也。因题诗于上,以志一生之痛。
为诗及跋语时他已八十五岁高龄,再过两年便下世了;他自叙五十余年中为她留下了“千斛泪”,而两人爱情终无结果则是他的“一生之痛”。持续了这样长久的情感在二十世纪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少见的奇迹。一九七八年九月谭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两人虽同在北京,却不能相见,这是最后一句诗之所指。
顾、谭往来最多的日子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到一九二六年六月这两年之内,以后便会少离多,主要靠通信来维持关系。下面我将就他们交往最密切的三个阶段——即一九二O年代、一九三O年代和一九四O年代——分别点出他们情感发展的高潮。由于我的基本资料是这部《日记》,事实上真正呈现出来的只是顾对谭的一往情深。顾先生在一九四三年曾自编一张《与健常往来年月表》(丁按:稍微有点发指的说),起一九二四,迄一九四二,颇便检查(丁按:余先生,表酱紫欠揍吧……)(见《日记》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条末),因此下文将略“事”而详“情”。顺便说明一下一九三O年代后谭慕愚的正式的姓名是“谭惕吾”,而《日记》则往往称她为“健常”,也许是她的字或号。
顾对谭似乎是一见钟情,交往十几天之后他在《日记》上写道:
以谭女士之疾,心甚不定。吾对她以性情上之相合,发生爱敬之心,今一闻其病,我之心搅乱乃如此,吾真不能交女友矣。(一九二四年月五月一日条)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条又记:
予与介泉言,如予者无资格入情场,而此心终不能已,缠绵悱恻,殆不可堪。思之良愧!自游颐和园至今日,才六十九日耳,乃觉有半年之久,时间之主观如此。
很显然的,一缕情丝已把他牢牢地缚住了。这种一见钟情之感是怎样触发的呢?他自己有一段描写:
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同年四月二九日条)
“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是一种孤高的风骨,顾自己也是如此,也就是所谓“性情之相合”。一年以后,相知更深,他又有进一步的分析:
予性有两个倾向,一爱好天趣,二勇猛精进。好天趣者,友人中如(俞)平伯、(叶)圣陶、介泉皆是,故甚契合。惟勇猛精进者乃绝少,而不期于谭女士得之。
情丝绸缪,非偶然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四日条)
同年十二月九日日记云:
得谭女士覆书,知其肯纳我言,极慰。她极勇猛,眼光又甚锐利,如得专心为学,定可出人头地。予交友多矣,如我之勇猛而肫笃者极少见,而不期于女友中得此同调。特其棱角太露,到处生荆棘,更使我悲伤耳。
可知他最心折于谭慕愚的地方是她的“勇猛精进”的气概。事实上细读一九二四至二六年的《日记》,我们发现:这两年中顾、谭两人同在生命里最旺盛、创造力最辉煌的时期,不过前者的领域是学术,后者则是政治而已。顾的“古史辨”运动即在此时跃起,他那篇著名的《自序》是在谭离京前写成的,她并且预读过原稿(见《日记》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及十月八日条)。她的国学基础很好(见《日记》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及二十一日条),最后入北大史学系也是接受顾的鼓励(《日记》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上引日记中“肯纳我言”,即指此,所以谭后来也一直把顾当作老师。但谭的志业在政治,是当时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下文将做交待。总之,他们两人都进入了“勇猛精进”的人生阶段,彼此深相契合,是很自然的。
他们最初交游时,顾尚独居北京,但同年九月十八日他的续弦夫人殷履安女士入都定居后,(丁按:五十九年后的这一天,伟大的ct大爷出生了)他的内心冲突便愈来愈掩盖不住了。他们是旧式婚姻,履安虽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但特以贤德著称,内而持家,外而待客,无不情礼周到,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所以顾在《日记》中也常常自誓决不背负履安。下面两个梦最能说明他内心的天人交战。(丁按:苗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梦中见一人,昏夜中可近而卒不近,予谓之曰:“我没有法子和你好,你也不值得和我好,我们还是永远留着这一点怅惘之情罢。”醒来思之,不觉泪下。时天未晓也。
梦中人当然是谭慕愚了。一个半月之后,同样的梦又来侵扰他了:
拂晓得一梦,去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感略同。履安外出,其人过来,遂与共候门。迄深夜而履安不至,二人相对,极温存,又极无奈。她道:“你感到兴味吗?”答之曰:“妹,我不敢以自己的快乐而把你牺牲了。”(丁按:怆然涕下)觉后思之,情意无尽。不期卧病之中,乃有如许闲情。(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条)
所以在整个第一阶段,他们并没有“谈恋爱”,而且表面上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女方尤其如此。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他写道:
慕愚来书,过于敷衍,使我不快。案头文竹,渐渐枯矣,交游之缘其将尽耶?三月十八日相对默坐两小时许,其最后之温存耶?思之惘然。
可知他们的感情表现仅止于相对默坐,彼此心中都荡漾着一丝温存的滋味而已。这无疑是一种纯精神的交流,也许接近所谓柏拉图式爱情吧。
谭慕愚至迟在一九二五年已成为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下,她参加了许多反帝国主义活动,表现了大无畏的勇猛精神。顾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的日记说:
《晨报》载三日YX队(按:即“五卅运动”)至东交民巷时,前队(北大)迟滞不进,有女士二人径前夺旗,曰,“时已至此,还怕死吗!”大队遂随之而进。至栅门,门紧闭,乃高呼而返。彭女士言谭女士当YX至东交民巷时极激昂,《晨报》所言,或即是她。十一日,谭女士来,询之,谓即彼一人。
顾对谭的“勇猛”气魄知之甚深,故读报即认定夺旗而进者必有谭慕愚在内。他为谭的爱国热忱所感,竟也抛下文字,参加救国运动。同年六月九日的日记说:
今晚谭女士来,面容憔悴,嗓音干哑,闻自沪案起后,每夜至二三时始得睡,早五六时即起,在救国团日夜操劳。她身体本弱,向不能迟眠,今因国事如此,令人泪下。我为文字所迫,无时间作救国运动,明日教职员本拟不去,今日她来,使我不忍不去。
这并不是顾因情有独钟之故,刻意夸张她的勇敢与劳绩。试读闻一多在一九二六年的一段生动描写:
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溷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无一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斫鼻端而已。(丁按:腥风血雨的骠悍人生,令人心向往之)女士尝于五卅运动YX时,揭旗冲锋,直捣东交民巷,故京中传为Chinese Jeanne d’Arc焉。此亦趣闻,不能不与同志言之浮一大白也。
闻一多当时属于“大江社”,也是国家主义团体之一。信中所言“女同志”即谭慕愚,可知她自上一年五卅YX一役已赢得“中国的圣女贞德”的尊号,何以知此女即谭,李璜记述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去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反俄援侨大会”云:
主席台系从后面上台,因之主席台后门必须把守,最为重要。于是我派台湾籍北大同学团员林炳坤与谭慕愚守主席台后门,因林身高力大,而谭系北大女生,当时风气,对于女子,尚不敢乱下拳头。我两次参加YX,察知军警也不敢捉女学生,而首次闻一多主席之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筹备会,亦谭女士大呼几声便吓退共党也。
与闻函相对照,即是同一人,绝无可疑。这次大会主席李璜最后也是靠“谭慕愚女同志以身护之”,才没有被……打伤。
合读以上三种来源不同的资料,则谭慕愚在当时北京救国运动中为一叱咤风云的人物,已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难怪顾先生对她如此倾倒了。
第二阶段的交往在一九三O年代,顾任教北平燕京大学,谭则供职南京政府内政部,南北互访,时复一遭,彼此之间的情感深化了。《与健常往来年月表》一九二八年条云:
予在广州,暑假中得高君珊女士信,悉健常在大学院作科员,不幸以党案被捕入狱,嘱予营救,予因致长信与蔡孑民、戴季陶先生,并发电,请其营救。与健常一函,托君珊转交,彼得此大哭,来书有“最知我者惟先生”之语。出狱后,东渡日本,学于东京高等女子师范。(是年未见面)
经过这一次患难,谭对他的“知己”之感自然加深了。当时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不仅共产党已成非法组织,反共的青年党也同样在取缔之列。所以谭被捕入狱。此案消解后谭才能正式进入内政部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顾先生到南京访谭,这是久别后很重要的一次晤面。头一天在火车上适逢大雪,他已心中忐忑不安,赋诗曰:
一天风雪冷难支,为约伊人不改期。我愿见时便恸绝,胜留余命更生离。(一月九日条)
第二天会晤后记:
不见慕愚,一年半矣。情思郁结,日益以深。今日相见,自惴将不止陨涕,直当晕绝。乃觌面之下,尘心尽涤,惟留敬念。其丰仪严整,消人鄙吝可知。今日天寒,南方诧为数十年所未有。彼为我买炭,手拨炉灰,竟六小时,我二人在一室中未曾移席。(丁按:几可列为一典)呜呼,发乎情,止乎礼,如我二人者殆造其极矣。(一月十日条)
可知谭慕愚自有一种高华的品质,使顾得儿女情怀升华为“敬念”,孔子所谓“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也许便是指这种精神境界。一个多月后他去北平整理谭慕愚历年写给他的信,对于她发出了高度的礼赞。
民十三(一九二四)迄今,慕愚寄我函件得九十三通,有许多未填写日期者,须考定其事实及所用函信笺,颇费事也。将慕愚寄我的信通看一遍,其人格直如晶莹之宝石,有良心,有志气,有魄力,洵为超群秩伦之材,而频遭夜行者之按剑,世无真知,我自喜为九方皋矣。
慕愚性格,备具男性的勇敢与女性的温存。故有坚决的意志与浓厚的同情心。上月我与之谈,谓我欲造成人才而别人诋我利用青年,我欲提倡学术而别人诋我好出风头。彼云:“假性情人是必不能了解真性情人的。”(丁按:慕愚姐姐!555)她所以知我为真性情,正因为她自己是真性情耳。(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日条。按:关于他们两人性情的异同,他后来做了一个详细的比较表(丁按:再度发指……是史家的小习惯么?),见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条)
由于顾先生对谭的爱情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提升到了纯精神的层次,他在这次六小时的拨灰长谈后,想出了一个“精神之结合”的方式,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他记道:
久欲写慕愚信,今日忍不住了。信中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着力,将来好于我共作一部中国通史(丁按:多么浪漫的想法,感人至深!),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只要她能答应,我的不安静的心就可安静了。
这是一封二千余言的长信(见二月五日条),竟很快收到积极的反应。二月十七日:
得慕愚书,承受了我的要求,自接信日期,每日抽出三四个小时读书,并作笔记,先从满蒙新疆西藏等问题做起。俟见解成熟,再作论文以锻炼发表能力。为之大慰。只要她的学问有成就,我的生命也就有意义了。(丁按:无语凝噎)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谭慕愚对边疆问题的兴趣此时已开始,后来更亲往绥远考察,并代内政部长写《内蒙之今昔》。这些活动直接影响到顾先生的研究方向。他告诉我们:
廿二年(一九三三)秋间健常随黄绍竑到北平,旋赴绥远,商议内蒙自治问题。过平时,健常曾至燕大我家一宿。自绥远归,又至燕大讲演,予受感动,遂有研究边疆问题之志。(《与健常往来年月表》)
甚至他最后决定到北京大学兼上古史课也是因为谭慕愚的关系。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条记:
张西山君转到健常信,悉健常以到内政部逾半年,例须由铨叙部审查资格,而渠已改名,恐北大预科毕业证书无效,嘱我向蒋、胡二先生言之。然我以耽浏览,来济(南)已逾期,审查期亦已过,怅甚。即写梦麟先生信,答应下学年在北大兼课事,请其即速证明健常资格。(丁按:按不下去了,蹲到墙角哭)
(一)(二) (三) (四)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