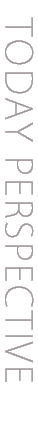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整体困顿 局部开花
──2007年小说综评
邵燕君
2007年又是文学发展相对平稳的一年。这平稳由一喜一忧构成。长篇之忧在于,自从2005年“长篇热”以来,数量持续上升,而佳作逐年见稀。不但一些“名家力作”名不副实,让人希望陆续落空,而且,随着“名家阵容”的日见整齐,当代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和前景问题,也越来越不容乐观;忧中见喜的是,虽然整体平平,但少数重要作品仍具有相当的价值——这价值有的来自作品本身的质量,有的得自其创作走向连通了当下创作潮流和文学史的重要脉络,而蕴含的问题又是触及了时代写作难度的“真问题”。中短篇中,让人忧的也是本该挑梁承重的名家精品数量太少,或许名家们都把精力投向长篇写作了。所喜的是,新锐发展势头颇旺,尤其是一批具现代形态的成熟之作较成规模的出现,显示了新一代作家们将现代技巧与自身经验融于一体的能力,让虚浮多年的“形式探索”终有落地生根之感,令人格外惊喜。
长篇力作稀而价值重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创作持续高温,目前年产量已是数以千计。而2005年开始的这一轮“长篇热”,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名家之作”云集——每年有10—20部“名家力作”被“隆重推出”,尤其年初时节,龙争虎斗,声势浩大。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图书市场的操作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有文学内部的动因。当代文学“新时期”以来各时段涌现出的著名作家,从“知青作家”到“先锋作家”,大都已过或已届天命之年,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期”也是“封顶期”。按照中国惯有的文学观念,大多数作家愿意以长篇创作来标识自己的文学成就。从这一角度看,近年来的“长篇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成就总结。然而,当我们以文学史的目光来打量这些作品时,每每多有遗憾。有的号称多少年磨一剑的作品,明显带有粗糙痕迹;有的有做“时代大书”的企图,却显露衰微之相。这一波“当代作家集中展现实力”的“长篇热”中,究竟有多少作品能够跨越“年度”,进入更长的文学史序列,恐怕不能乐观。
本年度,值得关注的长篇主要有:阿来《空山2》(《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轻雷》(《收获》第5期)、池莉《所以》(《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炜《刺猬歌》(《当代》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佩甫《等等灵魂》(《十月.长篇小说》第1期,花城出版社)、盛可以《道德颂》(《收获》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刁斗《代号:SBS》(《花城》第1期,花城出版社)、王安忆《启蒙时代》(《收获》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格非《山河入梦》(《作家杂志》长篇春季号,作家出版社)、朱辉《天知道》(《钟山》第2期)、李锐/蒋韵《人间》(《收获》长篇春夏卷,重庆出版集团)、孙慧芬《吉宽的马车》(《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2期,作家出版社》、张者《桃花》(《花城》第3期,长江文艺出版社)、董立勃《白麦》(《当代》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韩东《英特迈往》(《花城》第5期)、贾平凹《高兴》(《当代》第5期,作家出版社),林白《致一九七五》(《西部.华人文学》第10期,江苏文艺出版社)、麦家《风声》(《人民文学》第10期,海南出版公司),等等。
其中,阿来的《空山2》和《轻雷》属“《空山》系列”中的三、四、五卷,在前两卷的高水准上继续推进,称得上是本年度长篇小说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贾平凹的《高兴》将“乡土文学”的创作引入到“底层写作”的潮流中,无论取得的成绩还是显示的“症候”都值得纳入文学史的脉络讨论。此外,李锐/蒋韵的《人间》、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刁斗的《代号:SBS》,或保持名家水准、或在原有创作轨迹上有重要推进,或在立意及形式上有实验创新,值得推荐。
阿来《空山》:艺术水准年度最高
自从2004年发表《随风飘散》(《收获》第5期)起,阿来开启了其构建“《空山》系列”的宏大进程。继2005年的《天火》(《当代》第3期)之后,本年度推出的卷三《达瑟与达戈》、卷四《荒芜》和卷五《轻雷》使原计划中的三部六卷中的“六枚花瓣”已绽放了五枚,大体样貌基本可窥。
“《空山》系列”无疑是极具野心的作品,阿来意图构建一部西藏社会的现代史诗——当政权交迭“尘埃落定”后,古老的藏族社会如何在外来文明的入侵和席卷下发生现代转型,其中,“原始的”、“自成一统”的藏族信仰传统和以“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冲突是作品处理的核心问题。目前陆续发表的五卷虽彼此之间没有紧密的故事联系,但有着相应的历史顺序,《天火》已写到“文革”,《达瑟与达戈》则是“文革”期间的故事,《荒芜》写到“三年自然灾害”,《轻雷》则进入了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转型时期。小说以“机村”为落脚点,正面书写各种 “革命”(物质的、精神的)发生的过程。与之相应,写法上也从以前的“寓言风格”转向“寓言”、写实并用,并且,写实风格明显加强(从迄今发表的《空山》第一部、第二部来看,组成每部的两个故事分别有不同的倾向,卷一《随风飘散》、卷三《达瑟与达戈》倾向于寓言式的书写,卷二《天火》和《卷四》《荒芜》倾向于写实。最新发表的第五卷《轻雷》则是一部颇为写实的作品,可以说是阿来作品中写实风格最强的)。
如此,在《空山》的写作中,诗人出身的阿来要面对两项基本能力的挑战:艺术上的写实功力和思想上的驾驭能力。
在写实功力方面,阿来给出的答卷漂亮得甚至超出人们的预期。特别是《轻雷》中主人公拉加泽里形象的成功塑造,完全可以作为“典型人物”纳入到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成长人物”(如《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序列中,也可以视为“新时期”继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之后,又一代“农村新人”的代表——这样坚实有力的人物形象没有出现在贾平凹的《高兴》里,却出于一向文风飘逸的阿来之手,不能不使人惊讶,也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思想驾驭能力方面,阿来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并不是说并非以思想见长的阿来在这方面也有惊人进展——而是面对复杂的文明冲突和社会转型,阿来聪明而自然地选择坚持传统的文化信仰。在他的笔下,“世道”再乱,天神的法则不会变;疯狂的是人,神永远保持清醒。在对藏族文化的理解上,阿来其实有着“本质化”的倾向:原来藏族社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朴素的、自足的、神性的,现代文明的一切都是疯狂的、物欲的、具有侵犯性、毁坏性的,尤其是对“革命”缺乏更全面、深入的现代性反思,这里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在“告别革命”的普遍语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但阿来是幸运的——信仰的神性使他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超离现实语境的限制和主流观念的保守性,同样幸运的是,佛教的包容、宽广和温和,使他面对外来文明的入侵,哪怕是毁坏,都以平静的心态接受,在叹息中悲悯,而不是简单地陷入悲愤。所以,阿来小说里的世界虽是复杂混乱的,但他的小说世界却是笃定明晰的;观念可能是固定化的,但“世界观”却可能是相对宽广的。或者说,阿来未必能驾驭这个乱象纷呈的世界,但他的神帮他驾驭了。
当然,如果以“经典”的标准来要求,《空山》还是有上升空间的。首先在思想深度上,虽然有“神”的福佑,但小说毕竟处理的是具有现代性和当下性的命题,笃定的背后是单纯还是洞悉,小说的境界和气象是不同的。其次,对于寓言和写实两种写作方式,阿来虽然表现出全面的才能,但尚未能更有机地将两者结合起来,从而使整部作品的艺术风格更圆融统一,更具创新性和独特性。另外,一些细部处理,似还可以进行更精细的打磨。其实,象《空山》这样一部具有如此丰富含量的作品,放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值得作家毕一生之功来成就,没必要太快速出笼。
在创作长篇的同时,阿来还写了一些围绕机村的小故事,如《瘸子,或天神的法则》、《自愿被拐卖的卓玛》、《脱粒机》(《人民文学》第2期)、《马车夫.喇叭》(《上海文学》第3期),等等。这些分属“机村人物素描”系列和“机村事物笔记”系列的故事,都收入名为《格拉长大》(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8月版)的小说集中。这些故事大都具有言简意赅的风格,如碎钻镶嵌在整部《空山》“花瓣式”的结构中。
贾平凹《高兴》:站在“乡土”和“底层”的交汇处
贾平凹的《高兴》推出后立即受到热切关注。其原因不仅因为这是作家继《秦腔》之后推出的又一长篇力作,更因为它所处理的题材——进城的农民工捡破烂的生活正是典型的“底层题材”。而这些捡破烂的农民是贾平凹的乡亲,他们从商州大地走来,从《秦腔》中的清风镇走来,人物原型都有名有姓。正如贾平凹跪在父亲的坟头说的:“《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后记》)也就是说,贾平凹沿着自己的创作轨道发展,随着自己“血缘和文学上的亲族”的生活变迁而推进,到了《高兴》,与“底层写作”正面相遇,由此进入了这一写作的潮流。
自从80年代中期文学开始“向内转”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实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中国当代文学对农村当代生活的反应几乎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中止了,此后的乡村只是奔向“纯文学”作家们的叙述容器。连贾平凹自己也是先进入“废都”,后“怀念狼”。以致于到2004年前后,“底层文学”发轫时,成名的“乡土作家”几乎集体缺席。至今,在“底层写作”中活跃的作家,大都是来自基层的中青年作家,著名作家只有刘庆邦一人,但他主要写的是中短篇。而贾平凹长篇的《高兴》的推出,不但提高了“底层文学”的整体质量,也使对“底层文学”的讨论纳入到“新时期”以来,乃至鲁迅以来开创的“乡土文学”的脉络。
站在“乡土文学”和“底层文学”的交汇处,《高兴》文学史价值在于,贾平凹这位从“新时期”一步一步走来的老作家,以其扎实的写实功底、深厚的乡土情怀,写了中国在跨世纪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小说开篇即表明故事的发生时间在2000年3月10日到2000年10月13日主人公进程和回乡之间),被以“大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挤压、剥夺、诱惑的农民,抛离土地,进城谋生的生活状况。小说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了这些被称为“破烂”的农民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他们身处底层,操持贱业,忍辱负重,也苦中作乐。对“破烂”这一与城市人生活关系十分紧密的人群,当代创作也早有关注,最有代表性的是池莉在《托尔斯泰围巾》(《收获》2004年第5期,中篇)中塑造的“老扁担”的形象。这个形象虽然颇为感人,但池莉始终是透过市民的目光去看,“老扁担”终究是一个被观察的对象,甚至带有“城里人”一厢情愿的理想投射。当“老扁担”的生活刚刚被打开时,小说戛然而止。贾平凹深入的正是池莉未能进入的世界,不但告诉我们这个群体当下的生活,更告诉我们他们的来龙去脉,他们的“高兴”与“不高兴”,以及“高兴”与“不高兴”的缘由。贾平凹在《后记》中说,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历史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下乡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有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应该说这样的写作目标,《高兴》在一定层次上达到了。
然而,和《秦腔》一样,《高兴》是一部充满了矛盾、困惑、茫然乃至症候的作品,而且,由于《高兴》没有像《秦腔》那样刻意用一种“反现实”的“生活流”的写法“记录”,而是采取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法叙述,使作品内在的矛盾更明显地暴露为艺术的缺憾。比如,作为一部靠“体验生活”获取素材的作品,《高兴》在细节上虽然丰富却不够饱满,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虽然生动却不够深透;“典型人物”刘高兴形象没有立住,人物性格分裂,而作为“另类”(贾平凹语)又不能代表他所属的人群。全书以拾荒者为表现人群,却以一个虚幻的爱情故事为情感和情节动力,并且,人物的虚幻性和主要情节的不可信使作品整体框架不稳,结构失衡。
虽然存在着这些明显的问题,《高兴》仍然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原因在于,这些问题不是贾平凹个人的,而是症候性地显示了“底层写作”和“乡土文学”在当代发展的深层困境。
近来,写“乡下人进城”的作品逐渐增多。除了受“底层写作”潮流的影响外,更有“乡土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中国当代作家中像贾平凹这样的“乡土作家”比例甚大,他们不但出身乡土,而且多年来仍以乡土生活为安身立命的写作资源。这些年来,随着城乡生活的巨变,作家熟悉的乡土世界已经瓦解,这正是贾平凹在《秦腔》中展现的。作家如果依然忠实于他笔下的人物,也必然要跟着“乡下人”进城。本年度,另一部写“乡下人”进城的重要长篇是孙慧芬的《吉宽的马车》,小说通过一个“懒汉进城”的故事,展现了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人物在城乡之间的挣扎,尤其是人物“内心风暴”写得细密生动。然而,和贾平凹一样,孙慧芬在新作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物一旦进了城,就对他们失去了把握和控制。作家对于笔下人物的真实生活处境缺乏感同身受的真切了解,却和他们一样对现实和未来感到困惑和茫然。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自然和作家“下生活”还不够有关(但必须看到的是,贾平凹和孙慧芬都是写作态度相当认真的作家,当代著名作家中能他们那样“下生活”的已经很少见。这提醒我们思考的是,在一个阶级已经明显分层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当年工农兵文艺的意识形态支持和制度保障,还要求作家们像过去那样“下生活”,不但“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在“感情上打成一片”,是否还有现实可能性?),不过,在更深层次上,仍是作家的思想困境问题。
“底层”问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等大问题,从“乡土”进入“底层”,作家立即面临在思想能力方面的巨大挑战。而贾平凹、孙慧芬等汉族作家显然没有阿来幸运,在阿来那里可以用信仰解决的问题,在他们这里必须用思考解决。从《秦腔》、《高兴》的后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年农村的衰败、农民工的漂泊,贾平凹是深怀哀婉、愤懑的,但却无力处理、解读这些问题。深深的困惑和矛盾、理智和感情的冲突使贾平凹在写作中不但难有明确的价值立场,甚至不敢有真实的情感态度。他尽全力压抑自己的厌恶、仇恨,强打“精神”高兴。这是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扭曲造作、虚浮无力、难以生根的原因,也是“乡下人进城”的故事最终只能寄身于一个情爱故事里的原因——小说中无法解决的矛盾需要一个精神上和叙事上的逃逸之途。
那些令贾平凹等作家深深困惑的问题,如社会发展的效率与正义,城乡关系、阶级差异等,也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被称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两派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至今很难说能有哪一种观点能获得“上下一致的认同”。也就是说,作家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必须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即使形不成完成的观念体系,也应该在对现实进行详细解剖中提出有深度的质疑。这也就意味着,今天要写出真正能够把握时代精神的作品,对作家思想力的要求,远比意识形态相对完整、知识分子尚未分化的80年代为高。然而,与之相应的实际情况是,恰恰自80年代末期起,文学界便与思想界日益分离、作家从知识分子中逐步抽身。目前中国大多数作家的思想水准实际上停留在80年代,对90年代以来思想界面对社会重大变迁的思考、争论少有了解和吸收。思想资源的落后和贫乏曾是是“底层文学”难以深入的症结,如今又成为“乡土文学”难以前行的障碍,也是这些年作家们做“时代大书”的企图屡屡落空的内因。
(一)(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